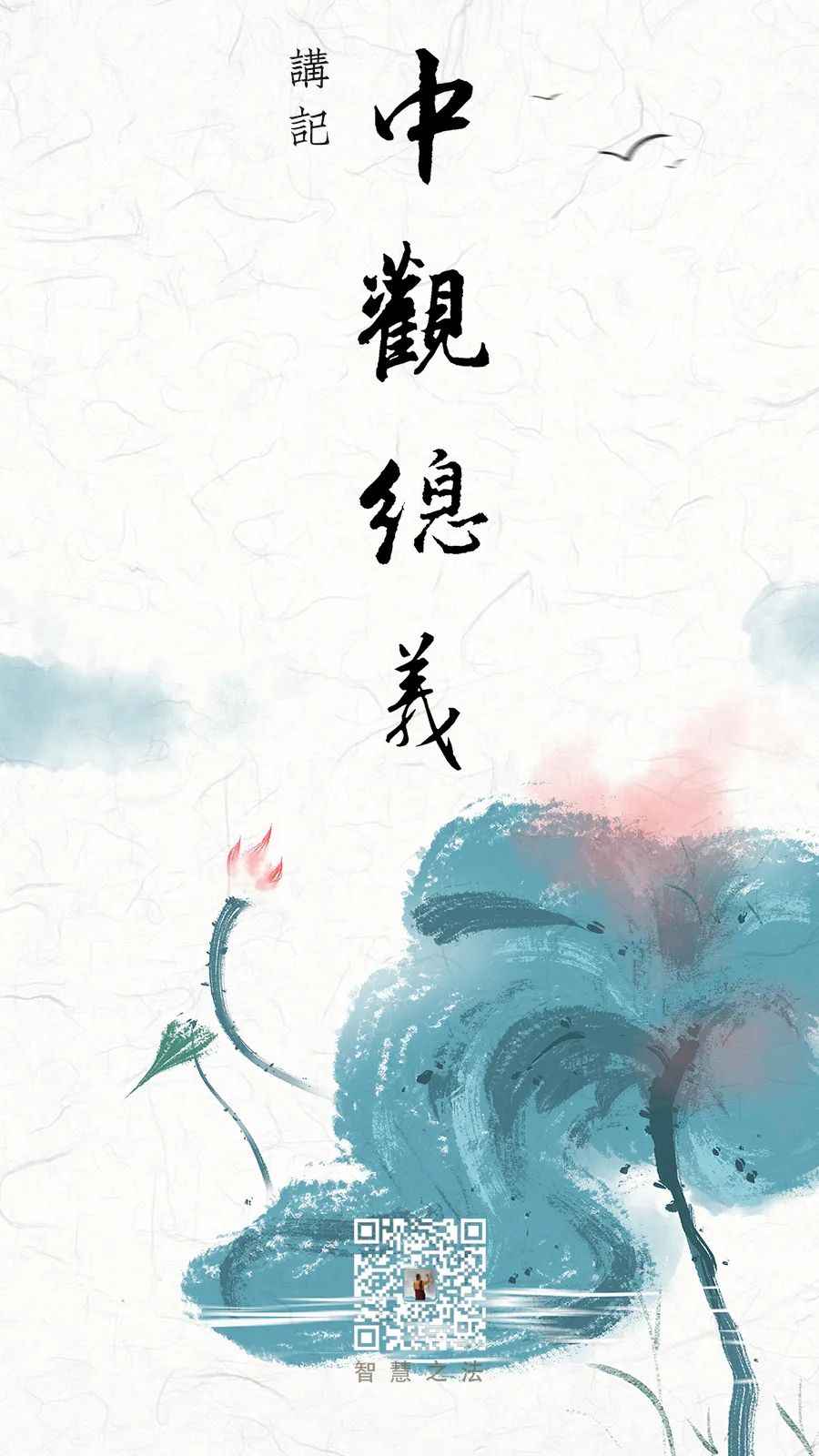
今天继续宣讲中观总义。现在宣讲中观自续派与应成派运用五大因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三、造成二派运用差别的原因
自续派和应成派运用五大因时有一些差别,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分析其原因也能够探究到二派在抉择空性时候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其实是根据所观察的不同层次,即观察空性、抉择万法究竟实相时,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有些是以比较浅的方式观察的,有些是以比较深的方式观察的。因此最初着重抉择真胜义还是假胜义,就是造成二派运用五大因差别的根本原因。分析这个差别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对于抉择空性的不同层次,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比如自续派1和应成派的差别是从根本上抉择胜义谛实相时究竟不究竟来辨别的。以自宗来说,《中观庄严论释》中说:“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胜义是自续派的法相,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则是应成派。《中观庄严论释》中全知麦彭仁波切讲,“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承认什么?承认世俗有胜义无,在世俗谛当中有显现,在胜义谛当中有空性。这种胜义谛是相似胜义,也就是假胜义。前面分析过,从自续派讲解抉择胜义当中空性这一点来讲,属于胜义,因为胜义理论是抉择空性的理论。因为他抉择出胜义谛空性的一分,所以是胜义理论。但是为什么说是相似的呢?因为他没有抉择一切万法实相的究竟大空性。所以既有相似的一分,也有胜义的一分,把二者合起来,就是相似胜义。“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则是应成派”,应成派抉择的既是胜义谛又是究竟真实的胜义谛。所以应成派是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而自续派着重讲解有承认的相似胜义。在安立此二派别的法相时,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以及应用正因的方式等差别来安立,仅仅属于支分的类别,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中。侧重讲解有承认的相似胜义是自续派的法相,和侧重讲解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是应成派法相,这个观点是自宗的观点。全知麦彭仁波切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安立自续派和应成派的法相的。这是根本的差别处。“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有些论师在区别自续派和应成派的时候,认为名言当中有自相成立是自续派,名言当中不承认自相成立是应成派。他们是从名言谛当中有没有自相的显现这个方面来安立自续和应成的不同之处;“以及运用正因的方式”,使用自续因是自续派,使用应成因是应成派,以此判别自续派和应成派的法相。但是麦彭仁波切说,虽然这个也是一种判别的方式,但是“仅仅属于支分的类别”,不是根本的分类方式,所以这个“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中”。有无承认、名言中是否承认自相成立、建立无自性采用应成因或自续因、对所破加不加胜义鉴别的这些要点都是以刚刚讲述的道理而出发的。”有没有承认二谛,名言中是不是承许自相成立,或者在建立无自性,空性的时候使用应成因还是使用自续因,这个前面分析过了。“对所破加不加胜义鉴别”,自续派对于所破的法要加胜义简别,即一切自生他生在胜义中是无自性的,加了个“胜义中”,所以加了胜义的简别;而应成派没有加胜义简别,直接说没有自生他生而破。对以上的这些要点“都是以刚刚讲述的道理而出发的”,刚开始时着重讲解承认是相似胜义,还是着重讲解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二派根本差别从这个道理出发,再从支分上安立有没有承认等其他区别点。在区分中观二派的差别时,后代的中观论师认为:名言中承认自相实有,是自续派;名言中不承认自相实有,是应成派。后代的一些中观师认为:自续派承许名言当中的显现法,而且显现法是有自相的。关于自相实有昨天也讲过,自续派的论师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谓的自相实有、有自相是它能够起作用。在名言谛当中能起作用的法就叫做有实法或实有法,名称安立成自相实有,但他说其实这个也是如梦如幻的,为什么如梦如幻呢?因为这些所谓的实有的法,通过胜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在胜义谛当中是空性的。既然这个法在胜义当中是空性的,那么名言当中的显现肯定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因为自续派在词句上说名言当中承许自相实有,不是无实有2,所以有些宗派区别二派时,从这一点说,所谓的自续派承许自相实有,而应成派不承许名言当中的显现法自相实有。也就是,应成派承许名言诸法是因众生的执著而产生的,是分别心假立,毫无堪忍的自体,因此不应当安立是自相实有之法,自续派认为世俗诸法存在实有的自体。应成派在承许柱子瓶子等诸法显现的时候,这些都是众生的执著而产生的,全都是分别心假立的,没有丝毫的自性勘忍的实有的自体。“因此不应当安立自相实有之法”,所以一切名言谛当中的法都是如梦如幻的。而“自续派认为世俗诸法存在实有的自体”。所以有些后代论师是这样分别二派的,而不是胜义谛当中是否抉择究竟空性。全知麦彭仁波切讲的很清楚,二派主要是在抉择胜义谛的时候,分不分二谛,或者着重承许有承认的相似空性,还是着重承许完全没有承认的真实空性。他主要是这方面出发来区别自续派和应成派的。但是有些后代论师认为,自续派和应成派抉择胜义谛上面没有任何差别,完全都是一样的。应成派抉择的空性也是单空,自续派抉择的空性也是单空的,从抉择单空、都要承认空性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差别。既然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二派的差别在哪里呢?他说主要的差别不在抉择空性上面,而在名言谛上面:自续派承许这些名言的显现是实有的,而应成派不承许这些名言的显现是实有的。他说应成派和自续派的差别单单是从这一点区别而出发的。这些宗派在其论典中讲得很清楚,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如果没有对空性有承认,不能对空性产生定解,也没有办法遣除实有的增益等。所以应成派在抉择胜义谛的时候,也是要分二谛的,也说胜义当中是空性的。当然这个方面不是应成派的真正意趣,他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宣讲的。所以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差别是名言谛当中承不承许实有。前代某些中观论师认为二派的差别是以胜义理论抉择的差别,自续派是使用自续理论抉择,应成派则运用应成理抉择。有些前代中观师讲到二派是在运用胜义理论的时候有差别,自续派使用的是自续理论,来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而应成派是运用应成理论去抉择。自续理论和应成理论前面已经介绍了。全知麦彭仁波切认为:上述“名言中是否承认自相实有”、“以应成理抉择还是以自续理抉择”等,都只是支分的差别而已。从某些角度来讲,上面所说的这些—名言当中承不承认自相实有,用应成理还是用自续理抉择等,也是区别二派的方式,但是这些都属于支分的差别,不是根本的差别。实际上,根本的差别是:一者着重抉择而宣说具有承认的假相胜义,另一者着重抉择而宣说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这个就是根本差别。下面还要分析这个为什么是根本差别,其他的为什么是支分。为什么这是二派的根本差别呢?因为其它支分的差别,诸如“有无承认”、“名言中是否承认自相实有”、“使用自续理论还是应成理论”、“对所破是否加胜义鉴别”等等,都是由“着重抉择相似胜义还是真实胜义”这一根本差别而出现的。抉择有无承认、到底有没有自相、有没有二谛的承认,或者世俗当中有没有显现承认,胜义当中有没有空性的承认等这些都是来自于“着重抉择相似胜义还是真实胜义”。因为如果着重抉择的是相似胜义,那么肯定要分开二谛,必须承许世俗当中有而胜义当中无;名言谛当中是不是承许实有也一样。如果着重抉择相似胜义,使用的因当然就是自续理论,因为抉择相似胜义的时候,他是分别心的境界,分别心抉择的时候他面前有共同显现,也有共同的有法、所破等,所以抉择相似胜义使用自续理论。如果抉择真实胜义谛,那么因为真实胜义是圣者入根本慧定的境界,是远离一切分别心的智慧,所以在殊胜的真实智慧面前不可能有自相成立、自他共许的这些有法,所以当然不能用自续因,要用应成理论抉择。“对所破法加不加胜义鉴别”,这个所破是胜义有,还是胜义没有,胜义中是空性的、没有的,世俗当中是有的。这个也是因为抉择相似胜义和抉择真实胜义的差别而出现的。(一)自续派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相(相似)胜义,故在胜义中有单空的承认,遮破自生、他生等后,安立无自生、无他生等。因为自续派最初就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相胜义(相似胜义),世俗当中有显现的承认,胜义当中有空性的承认,因此他在胜义当中承许单空3。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必须要了解,所谓的单空并不是自续派独有的名词名称。其实真正的单空分了两种,有暂时的单空和究竟的单空。暂时的单空以自续派为代表,自续派在抉择暂时单空达到究竟了,因为他把一切的色法和一切的心法都抉择为胜义当中无生,他把一切的所破在胜义当中都遮破完了。为什么他是究竟暂时单空的代表呢?下面的唯识宗,或者小乘的有部派、经部派也是有单空的抉择的。比如小乘抉择无我其实也是一种单空,是单空的一部分,为什么是单空的一部分呢?因为他抉择了粗大五蕴是空的,而无分微尘、无分刹那这部分的空还没有抉择。所以他的人无我属于一种单空,破了一部分有边之后他承许的一种单空。但是还剩下一部分的有边没有破,比如无分微尘、无分刹那,所以他的单空只是部分的单空而已;缘觉在抉择这个空性的时候,粗大的五蕴抉择完了,然后声闻中剩下的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这两个实有法当中,他继续把微尘这部分破完了,只剩下无分刹那的心识没有破,所以他这种也是单空的一部分;唯识宗他在抉择色法的时候,色法的本体空性离四边,但是在抉择二取空的时候,他没有真正抉择到离戏的空性,因此也算是单空的一种部分。自续派不管是从粗大的色法心法还是从细微的色法心法,他都抉择为了空性。所以他抉择的空性是究竟暂时的单空,胜义当中没有任何承许。但是这个方面只是暂时的单空而已,真正究竟的单空是什么?按照全知无垢光尊者最了义的观点,最究竟的单空是应成派的单空。究竟单空是什么意思呢?究竟的法界的自相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但是应成派只抉择了大空性这部分,没有抉择大光明(如来藏光明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单单的空,这种单空是究竟的单空。这个究竟的单空不是从空的侧面来讲,空的侧面来讲他已经圆满了,没有任何保留的。但是三转法轮抉择的他空如来藏、显现的光明藏这部分,应成派的论典当中没有抉择,他只是抉择了究竟离戏空。因为圆满的法界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的自性,但是应成派只抉择了大空性这一部分,而大光明这部分还没有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单空,但是这个单空是究竟单空。所以在分别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承许。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应成派是抉择单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惊讶,因为从如来藏,圆满法界的侧面来讲,的的确确所有应成派的理论没有抉择如来藏如何存在的,如来藏常乐我净的自性没有抉择。这些抉择如来藏存在的理论只是在三转法轮的经典,比如《宝性论》、《法界赞》等当中才出现。所以因为应成派没有抉择这部分的缘故,他也叫做单空,是究竟的单空。自续派在抉择这种单空的承认之后,“遮破自生、他生等后,安立无自生,无他生”。因为他抉择的是相似胜义,所以他当然是有承认无自生、无他生等的空性。应成派着重抉择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故在遮破自生、他生等戏论后,自己没有任何承认。应成派抉择的是真实的空性,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谛,所以他在破自生之后不承许无自生,破了他生之后不承许无他生。破了显现之后,承不承认空性呢?空性也不承认,因为所谓的空性是观待显现才有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显现存在是一种分别念,然后这个抉择空性是以另外一种分别来遮破更粗大的分别,以后者更细的分别来遮破前面更粗大的分别。最后通过观察抉择诸法是空性的,其实我们认为诸法是空性的,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分别念,但这种分别念可以遮破前面那种分别念。因为众生最粗大的执著无外乎就是认为显现的是有的执著,所以我们认为他没有、是空性的这个执著可以打破前面认为诸法实有的执著。然后这个空的执著也需要打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如果执著空性是实有,过失非常大。在《宝积经》当中讲:“宁执有见如须弥山,不执空见如芥子许。”宁可执著一切诸法存在的这个观点犹如须弥山一样大,也不能执著微细的连芥子那么大的空执。为什么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是针对普通的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宁执有见如须弥山”,你对有因果、有前后世的这种执著很大也不要紧,因为你毕竟相信因果,相信前后世,相信有解脱,你愿意去积累资粮。但是如果你刚开始就执著一切都是没有的,什么都不存在,没有前后世,没有因果,那么过失就非常大。这个是第一种解释的方式;第二种解释的方式:认为诸法有的执著可以通过空性的方便来打破—你认为是有的,我可以用空性来打破你。但是如果认为空性是实有的,那么用什么来打破他呢?真正打破执著的就是空性,但是现在把空性执为实有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把空性的执著打破呢?就好像药是治病的,服药可以治病,但是最后药在身体里没排出去,这个药本身变成了毒,那么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排出来了。所以本来执著诸法实有是一种病,这种病可以通过空性这种药来把它排除掉,但是如果这个空性没有消化,执著空性是实有的,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把空性的执著打破呢?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抉择的时候,“宁执有见如须弥山,不执空见如芥子许。”有些人不通达这两者,就用这个教证来说,不能抉择空性。这是错误的认知。其实真正的意趣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不能妄执断空,我们要认为有因果,有前后世等。在最后抉择空性的时候,我们不要执著空性是实有。所以也就是应成派讲的,显现也是无自性的,空性本身也是空性的,既不执著显现,也不执著空性。现即是空,空即是现。我们执著显现的时候,用空性来打破对显现的执著,所以现即是空,或色即是空,显现就是空的,我们打破对显现的执著;了知了空性之后,空性是不是存在的呢?空即是现,打破了对空的执著。现即是空,空即是现其实双破了现和空的两种执著。破完现之后不是承认空,破完空之后不是承认现。如果我们不通达,不善巧的话,我们会认为色即是空,所以空是有的,应该承认空;然后空即是现,现又是有的,好像大象洗澡一样永远没办法了,当你执著现的时候用空来破,当你执著空的时候用现来破,最后两个都破不了,好像最后破来破去两个都存在了,空也存在,现也存在了。但是真正的意趣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意趣是破的,因为所有的般若经是破戏论的,所有自空经论是遮破的理论,所以我们的重点不能放在立,建立了一个现就是空的缘故,建立了一个空就是现的缘故,不是从建立的角度讲的,而是从遮破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我们的方向应该放在遮破方面,遮破方面怎么理解呢?现即是空不是安立了空,而是遮破了显现的执著,空就是现不安立了现,而是遮破了空的执著,所以最后通过现即是空,遮破了对显现的执著,空即是现,遮破了对空的执著。显的执著也破掉了,空的执著也破掉了,这个就是真正般若经要给我们传递的,一切分别心面前没有任何可执著的信息和殊胜的见解。(二)自续派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相胜义,故在名言中承认自相实有,不能遮破。自续派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相胜义,所以名言当中承认自相实有,不能遮破。他为什么会在名言谛当中承许有显现?因为他抉择的就是假相胜义的缘故,所以他不能够遮破名言当中的显现。应成派着重抉择无承认的真实胜义,故名言中不承认自相实有,因为应成派着重抉择的是没有任何承认的真实胜义谛,所以在名言当中不承许这个自相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在圣者的根本慧定当中,一切的能取所取都已经熄灭了,没有任何所谓的共同显现分存在,所以他随顺于根本慧定抉择万法实相的时候,当然没有任何承认。而自续派抉择假相相似胜义,他其实是分别心面前的心所妙慧,不是真正根本慧定的智。心所妙慧是分别念状态的缘故,所以分别心面前肯定是有显现法存在的,所以这些显现法名言当中是存在,有显现而且是有作用的。再者,自续派着重抉择有名言显现的共同承认,及有胜义单空承认的假相胜义,自续派是两种承认,一种是名言显现的共同承认,第二是胜义单空的承认。世俗当中有有的承认,在胜义当中有空的承认,故他运用的是自续理论,他的有法是共同显现,他的所立是空性,他使用的因也是自他共许的法,所以这些比喻全都是自他共许的。这个所立的空性首先是自己承认,对方不承认怎么办呢?对方虽然不承认,但是要通过比量,让对方最后在相续当中产生一切万法空性的所立。最后三相推理抉择完之后,首先空性是自己相续承认的,然后以三项推理通过逻辑打破了对方的执著之后,对方相续当中也可以生起诸法是空性的所立,所以这个所立从究竟来讲也是自他共许的。应成派着重抉择无承认的真实胜义,由于自己无承认,故运用的有法、因、喻都是他方所承认的,唯以他方所许,遮破他的戏论。因为应成派抉择的是真实胜义谛,所以在根本慧定当中没有有法,所诤事的有法不是他自己承许的,空性也不是他自己承许的。不单单是单空不是他承许的,即便是应成派所谓的离四边的大空性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所承许的,离四边的大空性本身也是无自性的。所以所立他自己也不承认,这些因他也不承认的,因为应承派安立的是一切万法无所承认的大空性。有法是对方承许的,而最后要在他相续中引发无自性的比量。这些根据是用对方所承认的论式来让其了知自相矛盾,所以是以他方承许来遮破他的戏论。在是否加胜义简别的方面,自续派承认有共同显现分和无自性的空性,因此它有二谛别别的安立。加简别说:“仅仅胜义中空,名言中真实有。”因为自续派抉择相似胜义,所以他承许共同显现,也是承许无自性的空性。他要抉择显现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要加个简别说胜义当中是空性的。应成派二谛中都不承认共同显现分,故不必加胜义的简别。应成派在二谛当中都不承认共同显现的缘故,所以没有必要加胜义简别,就像昨天讲的,月称论师说加胜义简别成为无用,在抉择真实义的时候加胜义简别有什么用呢?胜义理论面前在抉择真实根本慧定境界的时候加个胜义简别,说胜义当中是空性的,这个没有用。因为圣者智慧面前所谓的世俗谛是什么,所谓的胜义谛是什么,所谓承认二谛到底是什么,其实根本来讲,在他的智慧当中一切的所缘都不存在,没有世俗谛就没有胜义谛,所以二谛都不承许的。反面来说,如果应成派自宗也有有法、因、喻、所立等的承认,则和自续派没有任何差别。反过来讲,如果应成派自宗有法也承认,因也承认,比喻、所立这一切都是自己要承认的,那么就和自续派没有任何差别了。应成派和自续派到底从哪个地方区分呢?虽然前面有些宗派说,空性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在名言谛上面有差别,但是后面很多自续派论师自己的论典当中讲的很清楚,所谓的名言当中自相实有的意思就是如梦如幻。并不像有些宗派讲的所谓的自相实有是堪忍的、不空的,自续派有应成派所发的三大太过等,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智慧品释》中说:“应成派此处唯一着重抉择离戏大中观的缘故,当知对此宗并无真假胜义的两种分类。”《智慧品释》是全知麦彭仁波切对《入行论》第九品智慧品的注释—《澄清宝珠论》。在《澄清宝珠论》中讲到,“应成派此处唯一着重抉择离戏大中观的缘故”,“当知对此宗(应成派)”,所谓的真胜义也是针对于自续派的假胜义安立的,究竟来讲,并没有所谓的真胜义假胜义的两种分类,直接讲万法是无自性空性的。因此,应成派最胜的优点即是唯一抉择真实胜义,不分真假胜义的差别,也就是全无承认,远离一切戏论。应成派最胜的优点是他最符合于法界自性,因为真正的法界自性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任何可以安立承认的法。我们凡夫人所认为的这些实有的显现,还有有些宗派暂时抉择所谓空性的自相,所谓的有和所谓的无,所谓的显现,所谓的空性,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真正究竟法界的本体。真正究竟的法界的本体不是任何分别心的所缘境,所以我们认为的有是分别心的所缘,我们认为的无也是分别心的所缘,我们认为的显现是分别心的境界,我们认为的空性也是分别心的境界,所以为什么说究竟的胜义谛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呢?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当我们在抉择万法实相的时候,认为是有的当然是错误,认为是空的还是错误。但是空可以打破有的执著的缘故,暂时来讲要依靠。虽然观待究竟来讲都不对,但是暂时来讲,认为诸法空性的执著可以打破对万法实有的执著。所以暂时我们要使用这样一种空执,然后当我们使用空执泯灭了对诸法实有的执著之后,我们再回头把这个空执也要打破,这样才能够趋入到远离一切承认的离有离无、离是离非的究竟的法界当中。因为菩萨安住这个境界而解脱,佛也就究竟现前这个境界而成佛的。我们要跟随菩萨和佛学习,内心当中也必须要生起这样的定解。当然这样的定解是超越分别心戏论的。如果我们没有真实通达空性所指的话,继续用分别心观察,用分别心的模式考虑胜义谛,总是觉得难以接受,和圣者宣讲安立胜义谛的理论有很大的出入,或者有少许的出入。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要经过不断的学习,让我们这样的执著,让我们的思维慢慢跟上这些佛经论典,佛菩萨的智慧,要把我们的智慧提升上去,而不是把佛菩萨的智慧拉下来,和我们的分别念平齐,觉得这样就舒服了、理解佛法了。其实这个不是佛法,它已经变成了你自己所谓的佛法,变成了世间法。所以我们要理解佛法,必须要舍弃我们的偏执,把我们的智慧提升到和佛菩萨的思维相同的高度,这时才可以舍弃我们执著世间的心,让我们能安住在随顺于菩萨道和佛道的修行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点痛苦,为什么有一点痛苦呢?因为我们所执著的这些早就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是有是无的这种思维模式了,因为这些思维模式我们经常用,所以觉得非常安全。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很熟悉的社区当中,我们在这生活,到处都是熟人,所有的商店我们都是非常熟悉,我们在这个很熟悉的环境当中,觉得非常安全。如果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当中,我们自然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什么,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到底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他的脾气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恐惧。同样的道理,是有是无等这样凡夫人的思维模式都是无始以来非常熟悉的社区,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我们觉得很熟悉很安全。突然来了一个一切都是没有的,有也是假的,无也是假的,然后要让我们修菩萨道,让我们出离,让我们修空性,一下子变成了很陌生的环境,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安全,有点很不适应。我们要花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它,必须要打破以前的执著。也需要一种正确的引导:没事,这里面没有什么是不安全的,其实这里面全都是好人,看起来很凶很可怕,但是他们都是很温和的,因为他的本性是菩提心、是究竟实相的缘故,所以不会伤害你。空性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很恐怖,什么都没有了,实际上真正去接近他,接受他的时候,最后就觉得他才是真正安全的,因为究竟的实相就是这个,这个是永远不变化的,永远不欺惑的一种圆满的自性。学《入行论》第八品也提到过,刚开始要我们放弃自己的执著去修利他心,一心一意要利他,感觉非常恐怖,但是慢慢接近他的时候,会越来越喜欢利他心,因为这个心很温和的、很柔和、很慈爱。当你生起利他心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温暖。从深层次的角度讲,真正利益众生的善心生起来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一种最大的安乐。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接近,很陌生的时候,会很害怕,但慢慢接近会越来越喜欢。空性也是一样的,因为大空性和大悲心、菩提心是法界的两个自性,不同的两面,所以当我们接近空性的时候,越接近空性越知道,的的确确这就是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永远不会变的实相。所以当我们最后抉择的时候,会越来越喜欢它。所以我们刚开始抉择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点痛苦,为什么会有点困难,用比喻做个分析就是这样的,应该可以理解。教证:
《回诤论》云:“若我有少宗,则我有彼过,由我全无宗,故我唯无失。”如果我有少许的承认,那么我就有上述的过失,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承认的缘故,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过失。《六十正理论》云:“诸大德本性,无宗无所诤,彼尚无自宗,岂更有他宗?”“诸大德”就是这些证悟者,佛菩萨等。一切诸大德所宣说的,或者所照见的万法本性是什么?“无宗无所诤”,没有任何安立、承许。因为无宗的缘故,没有任何的争论。“彼尚无自宗,岂更有他宗”,这些大德所发现的、所抉择的本性,尚且没有自宗的缘故,何况有他宗的承许呢。所以自他共同的承许都是没有的。《四百论》云:“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寂灭,于中欲兴难,毕竟不能申。”这个颂词是《四百论》的最后一个颂。记得好像是当中观师打破了一切邪执之后,有一些假许的所破的对方,或者外道或者分别念,说,现在你们是很厉害,通过前面的胜义理论观察之后,的的确确把我们所有的安立,所有的宗派都破完了。但你们也不要得意,虽然现在这个时代找不到破你们空性的人,但是在以后的时间当中肯定会出现比你们还要厉害的人,用更圆满的理论把你们的空性推翻掉。颂词的前提是这样的。圣天菩萨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呢?“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寂灭”,你不要妄想以后还有人会推翻空性,因为所有的执著都安立在世间当中,有是一边,非有是无边,聚(二聚)是亦有亦无边,非是非有非无双非边,所有的执著包括在有无是非四边当中,怎么去寻找也只是有这四边。“诸宗皆寂灭”,一切的承许—有的承许,没有的承许,二聚的承许,双非的承许,全部都已经寂灭了,没有任何承许。“于中欲兴难”,“中”字就是在空性,一切万法无有承认的本体当中,你想要兴风作浪,想要给中观空性提出一些妨难,想要给中观空性提过失,“毕竟不能申”,毕竟没有这个机会,不要说现在没有,以后永远也找不到推翻一切万法空性的观点。因为远离一切承许的缘故,如果有少许的承认就会有矛盾、过失,没有少许承认的缘故,任何过失都没有办法安立。《显句论》云:“凡中观师,理不应用自续比量,不许他宗故。”《显句论》说:凡是中观论师,在这个道理上,都不应该用自续的比量,因为不承许他宗的缘故,自宗也没有,他宗也没有。通过对方应成……的过失破邪执的意义“亦唯属他”,只是他宗才有,“非属我等”,我没有这些过失,为什么呢?“自无宗故”,自己没有所承许的缘故。《入中论》云:“能破所破不合破,及合而破所说失,若定有宗彼成过,我无彼宗故无过。”自己无宗故,无法对自己发出太过。能破所破合不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对方发了过失,因和果之间是接触而生果还是不接触而生果?如果接触而生果,因果成一体,不接触而生果,东边的种子可以在西山结果。对方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你们中观师破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观点是所破,你们中观师的理论是能破,现在我要观察一下,你的能破和我们的所破接不接触。用同等的理论观察你们的能破和所破到底合不合呢?是接触而破还是不接触而破呢?他就觉得找到了一个推翻中观的机会了。“能破所破不合破”,如果能破和所破不接触就能破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随随便便就可以破了,因为根本不接触就能破的缘故。就像东边的人不接触西边的人也能打到他。所以能破所破如果不合而破,有这样的过失。“及合而破”,如果能破和所破接触了,那么能破和所破就成一体了,能破就是所破,所破就是能破了,谁破谁呢?一体当中自己破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能破和所破接触而破有这个过失,不接触而破有另外的过失。那么你们中观宗的能破和所破接不接触而破?中观师说这个没问题。“若定有宗彼成过,我无彼宗故无过”,其实我们自己的宗派只是为了推翻你们的邪执而已,我们自宗是没任何承认的,没有任何承许说我们的能破是实有的,所破是实有的。如果能破和所破真正有实有的安立,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说法,因为如果能生因和所生的果都是实有存在的,就可以有这种详细的观察。但如果没有实有存在,只是破你们观点,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我们自宗并没有承许能破是实有,所破是实有,没有这样的前提,当然就没有任何过失了。所以对方用这个方式也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破绽。“自己无宗故”,不是中观师很狡猾,没让别人抓到破绽,而是的的确确没有,因为他没有任何承认的。如果中观师承认能破,他肯定有这个过失,怎么也跑不掉的,但是因为中观师的确没有承认,给别人讲的时候也没有承认,自己内心当中也是没有任何执著,任何承认,所以这个没有任何执著,抉择法界的时候,怎么给他安立任何少许的过失呢?完全没有。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疑惑、问题,其实在《入中论》等这些大论典当中都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能认认真真地学习佛法,我们的所有疑惑都可以逐渐逐渐次第次第地予以遮破。凡夫人的分别念和圣者智慧的确是没法比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很敏锐,找到了一个什么所谓的过失,但真正来讲凡夫人的思想再怎么敏锐也没办法和无分别智慧相比较。《入行论》云:“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故中观师的一切建立都仅是就他方而安立的。《入行论》这个颂词,实有的法和无实有的法都不住在心前的时候,心前没有任何相可执著,所以自己的心也就安住在无缘最寂灭的状态当中。《入中论》云:“如汝依他事,我不许世俗,果故此虽无,我依世说有。”中观师破掉了对方的依他事—依他起,对方说我们的依他起不成立,你们的世俗谛也不成立了。中观师说,“如汝”,就如你承认的实有的依他起,“我不许世俗”,我不承认像你们承许实有的依他起一样,承许一个实有的世俗谛。因为我不承许实有的世俗谛,所以我不像你们一样有过失。“果故此虽无”,虽然世俗谛在胜义当中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但是“果故”,有必要的缘故,“我依世说有”,我只是依靠世俗谛说有。《回诤论》云:“所破无所有,故我全无破,是故云能破,是汝兴毁谤。”此说破他宗也没有。这一颂词是破他宗也不存在的。“所破无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破在我的境界当中是没有的,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所破。没有任何的所破的缘故,也没有任何的能破。“是故云能破”,你说我有能破,“是汝兴诽谤”,是你在诽谤我。归纳起来,中观师既没有真正的所破,也没有真正的能破可以安立。所以真正是诸宗皆寂灭。只因对方有承许,所以把对方心中的执著安立为所破的执著而已,自宗是没有的。宁玛派自宗认为:事实上,自续派也不承许单空为究竟实相之义,其最终承许的胜义谛也是远离四边的大空性,不许任何破立之法,故和应成派并无二致。这一点,从自续派论师们的论著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来。前面讲到了自续派和应成派的一些差别,但是这些只是暂时的差别而已,因为他们在最初着重抉择相似胜义这一点上和应成派是有差别的。但是究竟来讲,自续派和应成派也没有任何差别。事实上自续派最究竟的时候,也不承许单空是究竟胜义。最终和应成派一样,承认远离四边八戏的大空性,他也不承许任何可破可立的法,所以究竟意趣和应成派没有什么差别。既然究竟意趣没有差别,为什么要分类呢?因为他最初着重抉择的是相似胜义,而应成派最初着重抉择的是真实胜义,从这个方面来分别自续派和应成派。虽然究竟上是一样的,但是从着重的角度、最广大的方面,自续派通过很多推理、比喻、因、大量的教证理证,建立了单空,他的最究竟的意趣只用一两句带过,说这个也不是真实的,然后进入到真实义当中,并没有广大着重建立真实胜义;而应成派用大量的教证理证建立了无自性,建立了真实空。所以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差别主要是从着重建立这一点,而不是最究竟的意趣。譬如,清辨论师在《掌珍论》第三品自释中说:“暂时承许单空为相似胜义,究竟则无任何承认,并且安立无分别自证的见解为远离一切承认。”清辨论师对《中论》的词句作了注释,叫《般若灯论》,就像月称菩萨对《中论》的词句作的注释叫《显句论》。然后清辨论师对《中论》的意义作了一个注释,叫《掌珍论》,好像手掌上面的珍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意思,月称菩萨对《中论》的意义作了注释叫《入中论》。清辨论师归摄了中观的修法,造了一个论典叫《中观宝灯论》,然后月称菩萨对中观的修法归摄叫《摄慧论》4。两大论师都有对《中论》的词句、意义,还有修法的归摄作了论典。《掌珍论》当中讲:“暂时承许单空是相似胜义,究竟则无任何承认,并且安立无分别自证的见解为远离一切承认”。最究竟来讲没有任何所承认的,而且所安立的这些无分别的自证的见解是远离一切承认的殊胜自性。所以从这些方面观察时候,他也认为最后是无分别的自证,不是妙慧心所。又在《归摄中观精华论》中说:“于假相胜义,真实胜义中,后者非意境,无任何分别。”在《归摄中观精华论》中讲:对于前面所承许的假相相似胜义谛,“真实胜义中,后者非意境”,“后者”就是真实胜义谛,“非意境”,不是分别意识的对境。“无任何分别”,远离一切分别念,远离一切有无是非的执著。又于《般若灯论》等中,引般若经论说:“胜义谛远离一切言思之境,寂灭一切戏论,乃为诸法之胜义本性。”在《般若灯论》中引用般若经中讲的:“胜义谛远离一切言思之境”,不是任何可以表述的,不是任何思维之境,所以“寂灭了一切戏论”。在我们的言思当中有无承认都可以有,但是究竟来讲,一切的说有、认为有,说无、认为无其实都是寂灭的,因为不是分别念状态的缘故。所以这个是一切诸法胜义本性。又于《中观宝灯论》中说:“究竟的修法超离一切寻思,不住任何边,分别心在任何法的本性中亦不生,应安住在何者亦不成立的本性中。”究竟的修法超离了一切的言思,不住任何边际,分别心在任何法的本性中亦不生,所以应安住在何者不成立的本性当中。智藏论师在《中观二谛论自释》中说:“遮遣一切生、住、灭,抉择为无生、无住、无灭,这个就是自续派的相似胜义,最初时着重抉择的,要破生、破住、破灭,而抉择或者承许无生、无住、无灭。其后指示:究竟的胜义空性中,并无任何可作破立之法,乃为'真实明无遮'。”究竟的胜义当中没有任何破,破的是什么?前面的生、住、灭;然后立是什么呢?无生、无住、无灭。首先是破了生、破了住、破了灭,这个是有破;然后也有立,安立了无生、无住、无灭的空性。但是究竟的胜义当中,既没有任何的破也没有任何的立,所以远离破立。“乃为真实”,“真实”是胜义谛,真实的胜义谛当中“明无遮”,应该知道这个究竟是无遮的,没任何安立的。静命论师在《中观庄严论》中云:“真实中彼离,一切戏论聚,……,若依分别念,成俗非真实。”在《中观庄严论》的颂词当中讲了,“真实”,究竟的胜义谛当中远离“一切戏论聚”。“若依分别念,成俗非真实”,如果依靠分别念安立有无,那么成了世俗谛,不是真实的胜义谛了。该论当中讲得很清楚,刚开始他们破了生而安住无生,但最后归摄的时候,“生等无有故,无生等亦无”,因为没有生的缘故,无生等也没有。无生空性首先是建立的,但是在究竟当中无生等也不建立,也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分得很清楚,究竟意趣上自续派应成派完全一致。很明显,自续派为了引导实执心比较粗重的众生逐渐趋入到究竟胜义谛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建立了以分别心能够很明显的或很容易通达的分二谛的观点—世俗中有显现,胜义中是单空。因为单空比较容易理解,把这个破完之后就是空性了,对空的认知比对离戏的认知要容易的多。我们说(离戏)有也不是,无也不是,它到底是什么?如果刚开始没有学习过这些过渡的方法,他根本没办法认定什么是“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他觉得不讲还好,越讲越糊涂,不是智慧品了,越讲越没有智慧了。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讲,分开了二谛,世俗是有的,世俗谛当中有显现,然后胜义谛当中是空性的无自性的,他这样就接受了。有在世俗谛当中是不破的,然后没有是胜义当中没有,而且这个无是可以认定的,他的分别心面前可以抓住这个无,抓住这个空性,有也可以抓住,无也可以抓住,他觉得能够理解。空性真正有所了解之后,最后再反过来讲:所谓的无是观待有才有的,所以“有”没有了“无”从哪里来?有了这样的铺垫,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刚开始给他讲非有非无,什么也不是有,什么也不是无,什么都不能执著,他根本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有这个过渡,他慢慢就可以接受了。其弟子莲花戒论师在《中观庄严颂难题释》中说:“暂时可以建立一个属于无边的单空,其单空在胜义谛本性中并不存在,因胜义谛远离四边八戏之故。”暂时可以建立一个属于无边的单空,这个单空可以被认定的。其单空在胜义谛本性当中也不存在,因为胜义谛远离四边八戏之故。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全知麦彭仁波切《中观庄严论释》中说:“这只不过是抉择胜义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诸位祖师入定后得的意趣是一致的。”怎么样抉择自续派和应成派,只是抉择胜义谛的一种方式而已。总的来讲,诸位祖师,清辨论师、智藏论师,还是静命论师、月称论师,或是寂天论师等入定和后得的意趣完全一致。只不过是为了度化众生,跟随不同众生的根基,有些论师扮演了抉择相似胜义的角色,然后有些论师扮演了另外一种宣讲真实胜义谛的角色而已。其实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是悲心切切的显现。就是因为他悲心强,尤其针对那些没办法直接入空性的众生,给他们安立相似胜义,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方法找到进入空性的门。我们在学习这些宗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安住在分别心面前的实执,宗派的偏袒,认为我们是应成派的随学者,自续派的一切论师、理论好像都不如理、不如法一样。不是这样的,真正来讲,一切祖师入定的意趣、后得的意趣,他们所证悟的完全一样,他们的悲心完全一致。只不过有一部分众生需要自续派,非常需要相似胜义;有一部分众生也直接可以需要应成派,所以祖师们相当于商量分工之后,决定你们去建立相似的,我们来建立究竟的,而且我们显现还要辩论,如果没有辩论,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辩论之后大家就知道,他是这样的,那是那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祖师们,这些大德都是一样的,是一种默契。(开会商量分工是开玩笑的。)其实他们都是圣者,在圣者意趣当中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清楚。有些人肯定需要去建立不了义的法,有些需要建立了义的法。又说:“此二宗派(自续、应成)究竟意趣无二无别、平等一味。如果有人想:这样一来,应成派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既然是究竟意趣无二一味,那么建立应成派有什么用呢?你直接学自续派不就行了吗?自续派刚开始抉择的相似胜义,后面又抉择了究竟胜义,那么应成派的安立就没有用了。并不会成为如此,因为应成派依理广泛全面地建立了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因为应成派着重抉择依理广泛全面地建立了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胜义是自续派的法相,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胜义则是应成派。”应成派一定需要有,因为自续派着重抉择的是相似胜义,对于真实胜义谛,他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没有着重抉择。所以要真正进入究竟胜义谛,还需要应成派的论典。因为他们的分工不一样,应成派着重抉择的是远离四边八戏的真实胜义,自续派着重抉择是相似胜义。这也是为什么全知麦彭仁波切要造《中观庄严论注释》。《中观庄严论注释》里面既广大抉择了自续派,把自续派抉择的过程,把自续派的意趣,把自续派承许的方法,详详细细做了抉择,然后也对应成派观点详详细细做了抉择。《中观庄严论》的颂词虽然着重抉择的是自续派的论点,但是麦彭仁波切在造《中观庄严论注释》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着重单空的方式来抉择,他是通过自续派和应成派相当于平等的方式来抉择的。自续派是如何抉择单空,然后怎么样跨越单空进入究竟的胜义谛当中;究竟的应成派的意趣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麦彭仁波切安住究竟的意趣是按照应成派的注释来解释《中观庄严论注释》。所以这个《中观庄严论注释》学完之后,对自续派和应成派的观点,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了知。所以如果你只是学《中观庄严论》,应成派这块就不太全面了,如果你只是学《入中论》,自续派这块也不是太全面,但是麦彭仁波切的《中观庄严论注释》在自续派这块是广大的建立,然后应成派这块也是广大的建立。所以相当于把《中观庄严论注释》学完之后,自续派应成派以平等的方式,都能够了知的非常清楚。应成派不共四大应成因
前面讲了共同五大因,下面讲应成派的不共四大应成因是如何安立的。即汇集相违应成因,根据相同应成因(是非相同之类推因),能立等同所立不成之应成因,他称三相应成因。所谓应成派的四大不共应成因,第一是汇集相违,汇集相违其实我们平时用的很多,比如你这个观点是相违的;然后是根据相同,前段时间我们也用了很多。比如如果这个理论可以成立,那么那个理论也可以成立,根据是相同的。用另外一种相同的根据来让对方知道,他不得不承认的问题。本来他不敢直接承认,但是根据相同的缘故,如果承认这个,那么那个也得承认,你想承认的和不想承认的都要承认;能力等同所立,能立是因,所立是所立的宗,所立和能立都不承认,如果所立不成立,能立也不成立,那么就不是正量的论式了;最后是他称三相理论,前面已经讲了。一、汇集相违应成因
汇集和相违,这里有一个汇集,有一个相违。应成派通过智慧观察,把对方论式当中发现不了的、分散的、相隔比较远的、隐藏很深的、很微细的矛盾的地方汇集在一起,让对方很直观地一眼就看到是矛盾的。有些矛盾对方自己发现不了,认为很应理,然后中观论师,或者应成派论师通过他敏锐的智慧把矛盾放到一起,让对方看这个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叫汇集相违。汇集相违就是直接能够看出、点出承许过程当中的不合理的地方。即把他宗承许的两个相违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譬如,数论外道说“稻芽在稻种中已有”,又说“稻芽从稻种生”,把相违的这两者汇集起来,就可以向他宗发出应成的过失:比如数论外道说,稻芽这个果在稻种的因当中已经有了,因为它是自生。自生即果在因中已经存在,既然在因中已经有了,又说“稻芽从稻种生”,已经有了还说需要生,这两者是很微细的相违,但是他们自己发现不了,认为这个是很合理的。应成派论师就把这两者相违的观点汇集起来,叫汇集相违,然后向他宗发出应成的过失。如果稻芽在种子当中已经有了还需要生的话,那么这种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所谓产生、出生的意义是先无而后有,刚开始没有这个果,然后它显现了叫生,比如工厂里面生产的产品也好,或者小孩子出生也好,其实都是先无而后有,但是这个果已经有还需要生,就成没有意义,或无穷尽了。这个就叫汇集相违的应成因。二、根据相同应成因
因相就是根据的意思。他的根据、理由是没有差别的,是相同的。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差别,所谓的“此”是对方自己承认的, “彼”他是不承认的。但是不想承认的“彼”的根据和他承认“此”的根据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承认这个,就必须承认你不想承认的那个;如果要否认你不想承认的那个,就必须要否认你承认的这个。譬如,他生宗说:“两个法虽然是他性,也可以以一法生另一法。”两个法是他性的,但是可以有这个法生起那个法。这个是他承许的。对此,以因相相同,发出太过:如果“是他性”也能生,应成火焰能生黑暗,火焰和黑暗是他性故。对方认为稻种和稻芽是他性的两个法,而且稻种可以生稻芽。第一是他性的法,第二个是此可以生彼。应成派论师说,如果是他性的也能生的话,那么火焰也应该能生黑暗。为什么火焰应该生黑暗呢?因为火焰和黑暗是他性的,这个是相同的。如果同样是他性的稻种可以生稻芽,那么同样是他性的火焰为什么不能生黑暗呢?他性的根据是一样的。我们问:你们承不承许稻种和稻芽是他性的?对方回答:承许。我们再问:你们承不承许火焰和黑暗是他性?对方答:也承许。你们这个根据是一样的吧?根据相同。他们只承认稻种生稻芽,不承认火焰生黑暗,但这个时候用根据相同的理论,不得不承认火焰生黑暗。如果稻种可以生稻芽,那么火焰也可以生黑暗,为什么?他性是一样的。同样都是他性,你的这个稻芽可以生他性的稻果,那么我的这个他性的火焰为什么不能产生他性的黑暗呢?根据是相同的。如果你说:我这个可以生,那么我们说:火焰也可以生。如果火焰不能生黑暗,那么稻种也不能生稻芽了,根据是一样的。三、能立等同所立不成之应成因
“能立等同所立不成”,即能成立的因、喻和所立同样不成立。我们首先说,你的这个所立没有办法安立的,然后他说,我的所立可以安立,再讲一些根据,我们说,你这个根据和你的所立一样,都是空性的,都是无法成立的。这个叫做能立等同所立不成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说而已,要通过他的推理推出来他的能立等同所立不成立。如《中论》云:“以空辩论时,若人欲答辩,是则不成答,俱同所立故。”“以空辩论时”,中观师在讲解空性的时候,“若人欲答辩”,有人对中观师说一些不空的理论,“是则不能答”,其实这种回答(能立)不成立,为什么呢?“俱同所立故”,和所立一样,都是有过失的,都是无法安立的。中观师自己安住在空性见解当中,和不承许空性的宗派展开辩论,对方说:“并非空性!如果是空性,则无轮回,无造业堕地狱,无成佛、成菩萨等。”这句解释“若人欲答辩”。这个诸法不是空性的,如果是空性的,那么轮回也没有了,也没有造业了,也没有造业堕地狱的果了,也没有成佛、成菩萨的果位了等等。这些是他想要成立诸法不是空性而是实有的一些能立因,他的所立也是实有,他的能立也是实有。“如果是空性的话,应该成……过失”,这是他的能立。其实你的这些因—所谓的如果是空性就没有轮回、没有业、没有成佛等等这些能立,其实和你的所立“并非空性”是一样的,都是不成立的。你的能立是‘如果不实有,就没有轮回、佛菩萨等’,你的所立为‘诸法实有’,不仅你的所立不成立,连能立也不成立,因为所立、能立皆为空性,以空性如何能抉择不空呢?”你的所立法其实也是空性无自性的。当然中观师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是有一系列的根据的,比如离一多因或者缘起因等。对方说如果是空性,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是在世俗当中成立的,只是世俗谛当中才有。其实你的能立说如果是空性,就没有轮回,那么我们问:“这个轮回是谁在轮回?”“众生在轮回。”“众生这个人我在哪里呢?这个人我和五蕴是一体还是他体?”我们再进一步抉择对方的能立的时候,其能立本身也是空性的。通过观察人无我和法无我空性,一个一个观察,这些安立全部都是空性的。首先中观师说,一切诸法是空性,离一多故。他把不空的法抉择为空性。对方说并非如此,如果是空性的,那么人怎么修道,怎么有轮回?我们再抉择你的这个能立本身也是空性的,为什么是空性的?因为所谓的轮回的人在哪里,所谓的人也没有实有,也是空性。所以你的能立等同所立,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所立、能立皆为空性”,全都是空性的,所以空性怎么能够抉择不空呢?通过空性没办法抉择不空。很多地方讲,当中观师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很多人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疑惑,然后会讲很多不空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样,讲的越多,最后得到空的见解越多。就好像烧了一大堆火,有人想把火灭掉,但拼命往里加木材,实际上加的木材越多火越大。同样,中观师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你说不空,因为如果空了就没有轮回了。中观师把你的这个“如果是空性就没有轮回”这个观点再观察时,你的观点成空性,增加了空性火焰的炽燃,相当于往火里加了柴。不加柴还好一点,火就这么大一堆,但如果拼命加柴,说这个不空、那个不空。其实把所谓不空的理论全部投进去,加一个进去中观师破一个,安立一个空性,再加一个不空的理论,中观师再破一个又抉择一个空性。你认为的不空的理论越多,往里面投的越多,空性的火就着得越厉害。最后把所有能想到的法都用来建立不空理论,结果所有的理论全部抉择为空性,空性的火最后完完全全烧尽一切实执。所以能立等同所立都不成立。不管怎么讲不空的理论、能立,其最后全部变成空性。四、他称三相理论
他称三相,即他宗所承许的宗法、同品周遍、异品周遍。三相理论昨天我们解释过了。首先宗法是能立,在因上面安立;同品周遍,能立和所立之间的关系,能立和所立是同品的,是周遍的;异品周遍,所立一退,那么能立就退。他称三相之应成因:举出他方所承许的因和比喻,反过来遮破他的所立,在他相续中引起比量。所谓的他称三相应成因,举出他方所承认的因和比喻,然后反过来遮破他自己的所立。因是他自己举出来的,他的比喻、所立也是他自己承许的,所以用他自己承认的因和比喻反过来把他认为不空的所立完全破掉,最后在他的相续中引起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比量。譬如,数论外道承许芽果自生,中观师遮破:芽果应不自生,自体有故。中观师说芽果应该不是自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体有的缘故。芽果、自体有都是他自己承许的,然后通过自己承许的有法和他的因,最后“不自生”,让他自己打破自己所谓自生的观点,引发不自生的总相。其中,“无自生”唯一是遮破他宗所承许的自生,并非自方成立“无自生”之宗。无自生是唯一用来遮破他宗承许自生的。不是中观师自方成立无自生的立宗,而是对方有自生的承许,为了遮破他的自生,而说无自生。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1自续派抉择相似胜义,及名言谛中运用因和各种有法。
2不能起作用的法叫无实法,能够起作用的法叫有实法。
3单空:只破了有边的空,称之为单空,不是双运的空性。
4即《摄般若波罗密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