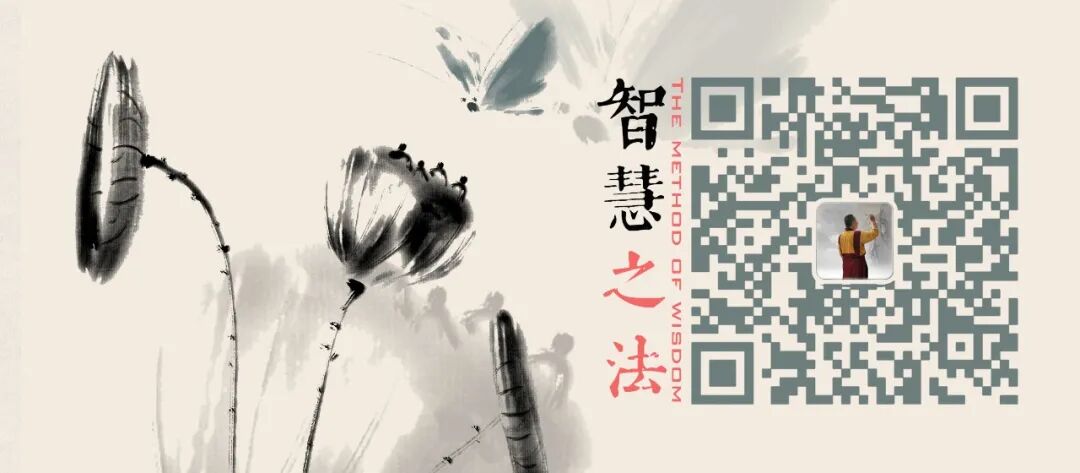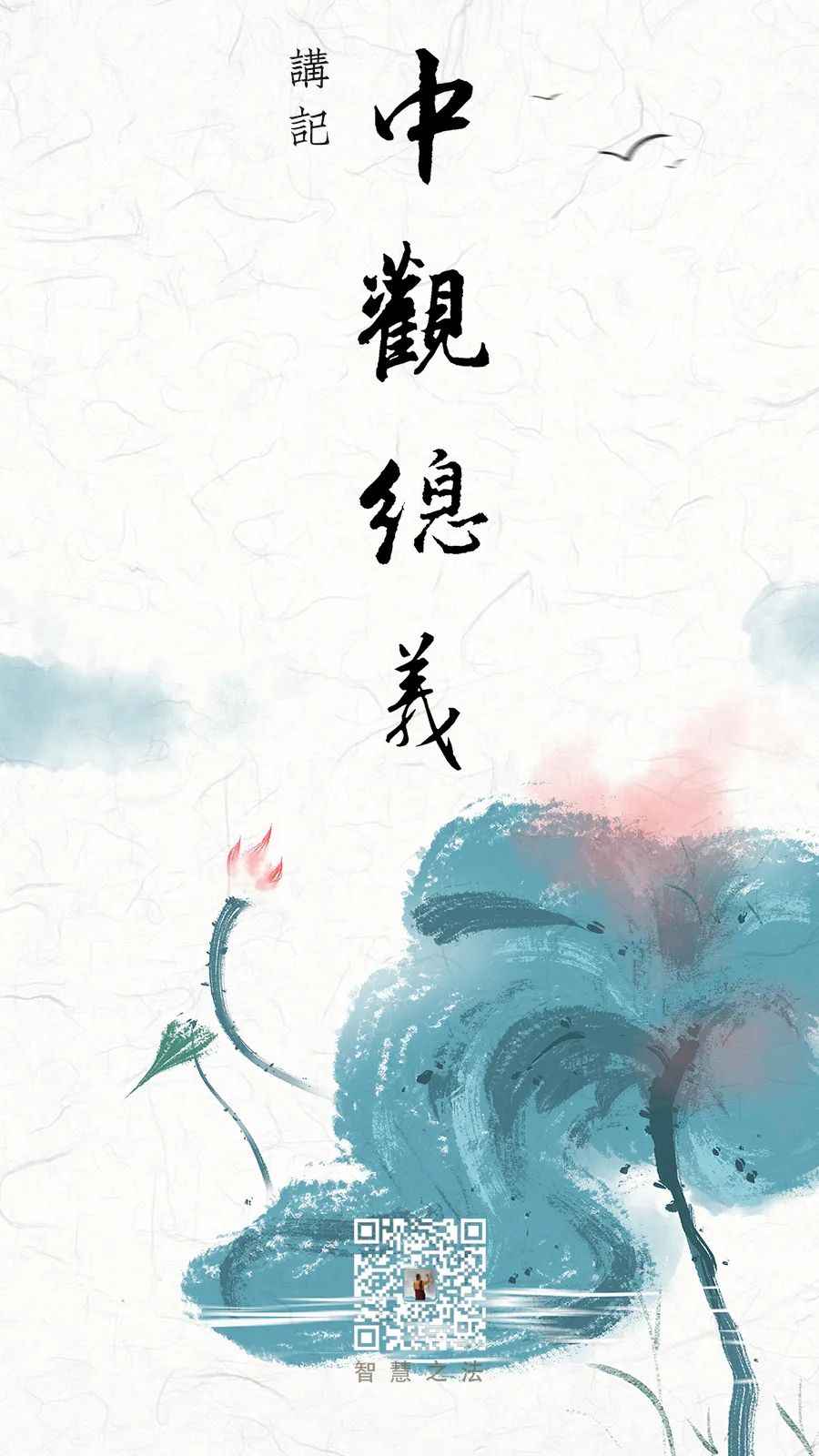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观总义》。现在我们学习到了通过能破来破所破,破掉了所破斥的所破法,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心上面。虽然有瓶子、柱子等等很多的法需要进行观察、抉择,但是其中1的原因之一是,一切外面的显现法其实都是心所显现的,都是心所造的。一切万法是心所造的,如果把心抉择为空性,就能够知道通过心为因而显现的外面的法是无自性的。还有心是根本的缘故,心的本性就是空性,心的本性就是光明如来藏,我们如果能够通过窍诀的方式来抉择心性无生,能安住心性无生,也就能够安住在心性光明的自性当中。
还有前面我们讲粗中观和细中观的时候,从修法窍诀的侧面来看,细中观在名言当中抉择唯识,已经把一切外面的显现法抉择为心识的自性,然后再把心识抉择为空性,那么一切万法能够了知是无自性的。所以,此处是通过五大因来观察心性无生,心性本空的状态。
前面我们通过金刚屑因、破有无生因和破四句生因的方式抉择了心是没有生处的。今天要讲第二: 因为离一多因是观察本体,此处是观察心的本体来了知心没有住处,既没有能住也没有所住。所住就是心所安住的地方,能住就是能够安住所住的心识。所住就是心安住的身体、外面的外境等可能的实有的住处。因为能住和所住是观待的,是一对,如果有了能住,就会有所住;有了所住,就会有能住。如果没有所住,能住安住在哪里呢?能住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如果只有所住,没有能住,这个所住是谁在所住呢?也没办法安立。因为我们执著这个心是实有的,既然心是实有的,就应该有一个住处—一个所安住的地方,我们就抉择这个心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所安住的本体。心如果有实体,应当有住处,所住是外境的色法,或者内的身体。前提是我们认为心是实有的,一个实有的法如果存在,一定有一个所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找它的住处。所住要么是外境的色法,要么是内的身体。如果心安住在外境的色法上,应当能在上面找到,但对色法再怎么分析,一直分到无分微尘,也不见心的踪影。如果心安住在外境的色法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个是我们在外境上面去寻找,把这些所谓的所住的色法,一个一个的分析,观察心识安住的迹象。因为心识就是一种能够分别的,能够安住、能明了的自性,我们在这些柱子、瓶子上面能不能找到能明了、能觉知的具有法相的本体的心识呢?其实我们是找不到的,从粗大的色法乃至于分析到无分微尘之间,上面都找不到心识的一点踪影,这个就是一种观察的方式。第二种观察方式,既然色法作为实有心识的所住,它的本体应该是实有的,但是我们观察这个色法,从粗大的色法乃至于分到无分微尘之间,这个色法的本身都不见踪迹,它怎么有可能成为一个实有的心识的实有的所住呢?它自己都找不到本体,就不可能做为一个实有的所住来成为能住心识的安住之处。这个是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如果心安住于内的身体,身和心要么一体而住,要么他体而住。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于内的身体上面,心和身体有能住、所住的关系,那么身和心二者之间,要么是一体,要么就是以他体的方式而安住的。如果是前者,应当有身时决定有心,这样尸体也成了有心。如果是前者,身体和心是一体的方式而住:因为身体和心就是一体的,乃至于有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有心,那么尸体是不是身体呢?尸体当然是身体,那么乃至于存在尸体的时候,也应该在尸体上面存在心。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尸体存在心,就不是尸体了,因为心识离开了身体之后,剩下的身体取名字叫尸体,所以如果尸体存在心,就不叫尸体,尸体上面绝对不存在心识。如果心以他体的方式安住在身上,要么遍满全身而住,要么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如果心识和身体是他体的,那么也只有两种存在的方式:要么心遍满全身而住,也就是心从头顶乃至于脚底遍满全身而住,要么心不遍满全身,它只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我们认为住在大脑当中,或者我们认为住在心脏当中。只有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心遍满全身,一个是心存在于身体的某个部位。如果遍身安住,应成全身的一切处都有心,砍断一节手指,应当砍断了心的一分;如果心遍满于身体而住,身体也是实有的,心也是实有的,而且心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上,那么当我们砍断一节手指的时候,应该就成了这个心就缺少一分了,这个心就不完整了。因为身体是实有的,能住的心识也是实有的,而且二者存在的关系是心遍满在身体上面。如果是这样,那么当身体缺少了一个分支,应该成了心识缺少一分。或者某些众生有特殊的因缘,他的分支比一般人多一些,比方手指、脚趾或者脚等比正常人多一些,应该成这个人的心比其他正常人的心多一分或多几分,那么这个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这样遍满的话,就有这样的过失。如果心住在身体的一方,比如住在上方,那在截断下肢时,应成毫无痛苦的感受。心遍满于整个身体也有它安立的地方,比如因为心识遍满身体的缘故,所以殴打、击打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疼痛。但是如果是心遍满于身体,就有上述不可避免的过失,所以就转移到另一种观察方式:心住在身体的某一方。心住在身体的某一方,固然可以远离上述的某一类过失,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其他没办法解释的问题。比如住在上方,心住在大脑当中,或住在心脏当中。如果心住在上方,心就不住在下方,那么在砍断下肢的时候,应成了所砍断的地方没有痛苦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心识不住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种观察方式,心是固定地住在身体的某个地方,比如心固定地住在身体的上半部分,那么如果已经固定在这儿了,那么砍断下部分的时候,就不会有痛苦。下面是第二种观点,心识住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可以移动。有人想:截断下肢时,上方的心识迅速移到下方,因此具有苦受。虽然身体住在某一部分,但是当下方遭受打击的时候,上方的心识马上就移到下方,就具有苦受。如果是这样,一个人遭到群殴,他的四肢,他的头、脚等很多方向都遭受殴打的时候,或者他的上下方同时被砍截的时候,因为他的心识只能够移到一个地方去,应该变成只有一个地方有痛苦,其他地方没有痛苦。因为截下方时,如果上方的心识移到下方,则上方无苦受;如果截下肢的时候,上方的心识移到下面,那么上面没有心识安住,就应该没有痛苦的感受,如果不移动,那么上方虽然有苦受,但是下方没有苦受,有这样的过失。如果心安住在心脏中,心脏成为它的住处,但是把粗大的心脏,一直分解到无分微尘,再抉择,连无分微尘也不成立,这样终究不见有一个实有的住处。以前有些人认为心识安住在心脏当中,现在很多人认为心识是在大脑当中。不管怎么样,大脑当中也好,心脏当中也好,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观察这些色法自性的大脑,或者色法自性的心脏,我们把粗大的大脑或者心脏,一直通过离一多因的方式分析,从粗观察到细,从细到极细,一直分解到无分微尘之间,再抉择连无分微尘也不成立。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毫不成立的地方,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实有心识的实有住处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以上观察了所住不成立。其实所住不成立,能住也就无法成立了。如果所住是无自性的,能住一定是无自性的。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所住上面住了一个无实有的能住;或者一个实有的能住,住在一个无实有的所住上面。因为一个无实有,一个实有,二者之间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联系的。就像兔角是无实有的法,我们的手是存在的法,我们可不可以用存在的手,去抓兔角,用这个兔角去挖地?这个不可能。所以一个无实的法和一个有实法之间没办法有任何的联系,如果之间要成联系,要不然都是实有的,要不然都是无实有2的。一者实有,另一者无实有,这个在《入行论》智慧品前面部分观察唯识观点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直接观察心识的本性。这个地方观待的所住把它安立为能住的心识。它有三种安住的情况:以色法的体性存在;以不相应行法的体性存在;以心法的体性存在。心识它只有这三种:第一种,心识是一种色法;第二种,心识是一种不相应行法;第三种,心识是一种心法的自性,就是心识的本体。如果以色法的体性存在,应当有颜色、形状、声香味触,首先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心识是实有的,而且它是一种色法的自性,那么所有的色法都应该有颜色、形状,在《俱舍论》当中颜色叫做显色,形状叫形色。比如它是圆形的、方形的,叫形色;这个色法是红的、黄的,这个叫显色。还有声、香、味、触,其实都是色法的一种自性。这个是显色方面,我们观察心识,心识是不是青的,是不是黄色的、赤的、白的?我们说心脏是红的,但其实并不是讲心脏的本身,前面讲过了,身体已经观察完了,心识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找这个心识的颜色,找不到。这个是显色方面找不到。长、短、方、圆,听不到声音,嗅不到气味,触不到软、硬等。长、短、方、圆这个是形色,心识即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方也不是圆。也听不到心识的这种声音,嗅不到心识的气味,触不到心识的软硬等。而且它的法相也相违。因为色法的自性都是有质碍的,就是有阻碍的,而心法是无阻碍的,所以从它的法相的角度来讲,二者之间也是矛盾的。比如身体不能够穿越墙壁,但是我们的心识就可以想:这个墙壁后面是什么,就可以很轻松的穿越,所以二者之间不是一种体性。如果心以不相应行法的体性存在,但不相应行法只是宗派的假立,此外没有一种真实的体性。不相应行昨天已经观察了,它是观待色和心安立的假立法,它只是一种宗派的假立,它是依附于色和心而假立的一种所谓的自性,它的本体是没有的,不像心法和色法有他们自己的自相,不相应行是假立的,所以没有自相可得。既然它没自相可得,它是假立的法,所以实有的心识不可能是假立的不存在的自性,二者3之间不可能是可以合理安立的。它能够了知的,是无质碍的,非色法的体性等,那么这个符合名言的体性。因为所有实有的自性,要么是一体的,要么就是多体的。可以以离一多因把粗大的心识逐步分析,最后分到无分刹那,无分刹那也抉择为空性。因此,心根本没有实有的一体或多体。前面我们在学习离一多因的时候,分别对色法和心法进行了观察。对于心法,把粗大的心识逐渐分析,抉择到无分刹那,最后无分刹那也是无实有的,也是空性的。如果我们认为心法的这个体性是实有的,那么应该经得起是一体还是多体的观察方式的认证,但是通过胜义理论去认证它的时候,最后它没有经受住考验,它已经瓦解了,自己慢慢消失了,没有了。它没有经得起考验的缘故,所以这个心识既不是一体也不是多体。既然心识既不是一体也不是多体,那么它就不符合于实有的概念,实有的体性就不具足了。所以心识不可能是实有的。通过上面以离一多因观察心的住处和能住的心,可以发现:心正显现时,内外周遍推求,也找不到它的住处,通过前面使用离一多因去观察心的所住和能住的这个自性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不是说心已经灭了,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再去寻找它的空性,不是这样的。在观察空性的时候,永远都是心正在显现的时候无自性。所以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执著的是正显现的心,而不是执著一个已经消失不见的这个心。我们说这个心消失不见了,不存在了,空了,这个不叫空性,只是说它没有,不存在了,或者说第一刹那的法第二刹那没有了,这个不是空性。空性的意思是正显现的时候没有自性,正显现的时候没有实有,这个就是空性。所以这里是强调这个问题,“心正显现时”,心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内外周遍推求”,从它的所住,从它的能住,从里里外外都去周遍、普遍的推求的时候,连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周遍推求寻找,也找不到它的住处。这个就是第二个解脱门空解脱门,它的本性是不住的,所以叫做空解脱门。如果我们要通过中观的方式修空性,那么就是这里面所介绍的方法。是不是唯一只能依中观的方式修空性呢?这个也不一定。前面我们介绍过一些密宗的生圆次第,还有大圆满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多证悟空性的方法。但是,如果是以显宗的方式来修空性,那么只有通过这样方式去观察心性无生、心性无住、心性无灭。我们说这个心在名言谛当中,有生,有来处,有住,然后有去或者叫做有灭,名言当中这个心识是有为法,它肯定是有生、住、灭。但是在胜义当中,心识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生找不到,它的住找不到,它的灭同样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法,即不存在生,也不存在住,也不存在灭。但它又能够起作用,起显现,怎么样才能理解呢?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名言谛当中这种心识是幻有的,是虚幻的,这种心识不是实有,是幻有。在胜义当中,这个心性无生、无住、无灭,它是当体即空的大空性的本体,大空性的实相。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心性,胜义当中完全大空性,名言当中它是如梦如幻。当我们通过胜义理论去观察这个心的本性,把这个心识观察完一圈,再回来,回到现实的心识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实有的心识是假的,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在上座打座的时候,观修心性本空,观察完起座之后,就发现,现在正在活跃的,正在移动的这颗心,其实是幻有的,是无实有的。这是通过观察完得到的,或者起定后得到的,自然而然能够了知它的无自性。因为在胜义观察,或者入座观察的时候,是直探它的本源,去找它的根,它到底是不是实有,这个心识法本身在究竟观察之后,发现它的确不是实有,的确是空性的。找到了根是空性的,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之后,再回到现在的心识当中,就知道这个心在显现的时候本空离根,它是没有实有自性的法,这个正在显现的心识确实是幻有,确实是无实有。其实我们观察其他的任何法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长时间用胜义理论观察这些杯子、花的自性是空性,一直这样观察,观察完之后,再来看这个花,我们就知道了,就在它正在显现的当下,的确是假的。虽然显现,但它的确是无实有的。这就可以引发一个很强的定解。这一念生起时,它不去其他处,因为这一念只有“去”和“不去”,当我们一念生起的时候,最后要灭,要“去”。这一念生起的时候,它其实是“无去”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去”、所谓的“灭”只是一种假相,真实来讲,没有一个实有的心识趋向于哪个地方。如果它是实有的法,这个法来了,住了,也会有“去”,也会有“去”处,也会有“去”者, 也会有“去”的方式。但是这个法是假立的缘故,所以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去”。因为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去”只是一个假立的“去”。在名言谛当中不能说它没有“去”,不能说这个心没有灭,名言当中有“去”,但是这个“去”实际上是虚幻的“去”,它是无实有的“去”,安立一个概念的“去”,安立一个名言的“去”,其实没有一个实有的“去”,这个必须要了解的。因为这一念只有“去”或者“不去”这两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如果是“去”,也不可得一个去,因为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有“去了的有去”和“还没有去可以去”的两种作业。我们已经确定这一念要么是“去”,要么是“不去”,现在我们首先确定是“去”,它自己是有去的,但是即便有“去”,也得不到一个实有的“去”,为什么呢?有两种情况,这个所谓己经安立的“去”,它是已经去完了呢?还是没有去可以去呢?如果这个“去”已经“去”完了,就不可能说“去”了的法还有“去”。去了的法怎么还有“去”呢?已经去完了,不可能再也重新“去”一次,如果去了还要去,就成了无穷无尽了。所以如果这个法已经是去了,已经消失了,它就不可能还有去。所以第一种“去了的有去”这个是不存在的。这种观察方式叫做胜义观察,都是严格观察。我们千万不要用名言当中这些思维的方式来套这种观察方式。有些时候,我们老是觉得想不通的地方,主要是把我们名言当中这些思想,放在了胜义理论当中去观察:这个不可能,这个好像是有相违的地方。胜义观察的方式是很细致的,很严格的。这个“去”已经去了?还是没有“去”可以去,如果已经去了,已经去完了的法不可能再去了,不可能有两种去,一个是已经去完了的法,一个还要再去一次,不可能出现两次。这个地方是从同一个“去”,不可能去两次,不是说名言谛当中去了外面,回来再去,不是说这种反复去。某个地方反复去很多次,这个是名言当中假立的去,我可以去很多次。这个地方的去是一个刹那当中,这个去已经安立了,而且是实有的,已经去完了,已经去了的法可不可能再去呢?它是实有的一体的缘故,去了的法不可能再去。所以如果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存在“去了的有去”。第二种,如果这个不是已经去完的法,它是还没有去,可以去,存在可去的可能性。如果是可以去,就说明它还没有去,可以去。它的重点是还没有去,虽然说可以去,但是它的本质是还没有去,本质和没有去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有去;还没有去可以去的法,也没有去。这两种情况,这两种作业都是不可能有的。前面说因为这一念,只有去和不去两种。去的情况已经观察了,要不然已去,要不然还没有去,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安立去。你既然已经确定它是不去了,当然就不是“去”。因为不去和去是矛盾的、相违的,所以不能说去。前面第一个直接观察去本身,叫做观察去者,这里第二个是观察去的地方,叫观察去处,比如我要去某个地方,我要去超市,我要去公园,观察他的去处到底有没有。从时间上分析去处,或是过去境,或是现在境,或是未来境。只有这三种时间安立的去的处。首先如果是过去的境,过去境灭了,不可能去。因为任何法都是刹那不住的,都是刹那生灭的,所以昨天的这个境,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乃至于前一刹那的境,在第二刹那都不存在。如果是过去的境,过去的镜已经灭了,已经不存在了,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法怎么可能去呢?所以这个过去的境不可能成为去处。现在境也不能去,因为现在这一刹那,如果是“正显现时”,就不能说是“去时”。现在的境,正在显现的时候,这个去也是处于现在时的。如果是“正显现时”,就不是“去时”,就不是已经去了,或者去的时。所以过去的境去不了,未来的境也去不了,现在的境也没办法去。因为现在这个正在显现的刹那,它正是显现,还不是去。如果我们安立一个和它相对应的名称,就是住,现在正显现的时候是正在住的时候,还没有去的时候。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去是已经去了,还是未来去,还是正去呢?和这个观察的方式也可以连起来看。其实已经去了的法,不能再去了,已经去完了。还没有去的法还没有产生。正在去,如果不仔细分析,有一个正去,我正在走,不是已经走完了,也不是还没有走,这个是不是去呢?其实正在去,详细分析的时候,也只能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去完了,一个是没有去。比如在《中论》当中分析过,走路的时候,正在走的这个脚为例,我的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中间划条线,脚尖放下去的时候,前面的部分是还没有去的地方,后面这部分是已经去完的,除了已经去和未去之外,找不到一个真正正在去的中间的这个时间,仔细分析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如果是粗大分析,有正在去的时候,脚正在动,正在去,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中论》第二品观去来品当中,把所有去的可能性都观察完了,去的动作,怎么安立去,去是已去,未去,还是正在去等,把所有可去的方案全部已经否定了。这个地方是以简略的方式来观察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去修持。真正比较详细了解,还是要学《中论》的第二品观去来品,讲的非常细致。一方面难懂一点,一方面如果懂了之后就非常殊胜,我们就知道没有丝毫的所谓的实实在在的去可得。心识如果存在,应该有迁变,生、住、异、灭。这个异也是包括在这个变化当中,住趋向于灭之间有一个异,异就是变化。前面讲了,有为法的完整的法相有四个:生、住、异、灭,这个异就是变化的意思。但是如果简略地讲,可以归摄成三个,就是生、住、灭,再简略就是生、灭。作为一个有为法的心识,如果真正实有存在,要么有生、要么有住、要么有异、要么有灭,那么异存不存在呢?这个变异也没有。如果是常法,不会迁变。当然已经常有了就不会迁变了。本来无常是可能有变异,但是这个无常的变异,只是名言当中有变异。用胜义理论做最严格的分析的时候,这一刹那的心,也不可能变异的。因为在一个刹那的时间中,正显现的同时,不会有变异。它正在生的时候,它不会有变;它正在住的时候,不会有变;它灭的时候,也不会有变。所以正显现的时候,这个变在哪里呢?在一个刹那这个时间段当中,找不到一个真正变的自性。迁变的自性是从住到灭的过程,有个转变。但是正在这一刹那,正在显现的时候,他正在住的时候不可能是异,正在灭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异。这个异只是从此到彼过程当中逐渐逐渐转变,那么这个逐渐逐渐转变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粗大的时间段,比较多的刹那当中才可以看出来它的变化,否则只是一个刹那当中是看不出它的变化的。当下这一刹那,怎么看到它的变呢?观察不了变。所以正显现的同时,不会有变异。所以生、住、异、灭当中这个变异也不存在。既然变异不存在,说明心识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一念心有灭,或者心是已灭,或者心是未灭,没有其它情况。如果心是存在灭的,那么这个灭或者是己经灭了,或者是没有灭,没有其它情况。如果已经灭完了,已经灭完的法连踪迹都找不到了,所以怎么会有灭呢?已经灭了的法,不可能再灭了,它已经不存在,就不可能有灭。所谓的灭是从有到无的过程叫灭,它已经灭完了,不可能再有这样过程。所以如果已经灭了,没有踪影了,不可能再灭。未灭的心也不可能灭,因为不灭和灭相违,不灭的时候决定不是灭。如果是没有灭,未灭的心也不可能灭,因为不灭本来就和灭相违的。不灭的时候,决定不是灭。前面的去和灭有时候稍微有点相似。去是正趋向于哪个地方,正在迁移,从此到彼,它是总的方面观察的;灭是彻底已经不存在了,一种空无的状态叫做灭。如果当下一念常有,应成没有变化,这明显和现量相违,如果这个心是常有的,那就成没有变化了,这个明显和现量相违。我们的心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说我们的心好难调伏,为什么心好难调伏?就是它在不断的变化。心识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的?如果它是有为法,我们就观察生、住、异、灭当中存不存在实有;要不然是常有的无为法,如果心是常有,和众生感觉的这个心识不断变化的这个现量明显矛盾,所以心是无常的,“刹那迁变,体无恒常”。名言当中心识绝对不是恒常的,名言当中不可能安立恒常,名言当中可以安立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是假立的,它不可能又是无常又是实有,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无常的心一定是无实有的法。如果一念心从生起到灭尽之间是常有的,不变化的。那就有以下的过失:一念心有生有灭,而且生起的第一刹那和灭尽的一刹那是完全不可分的一体,那么就应该有以下过失:所谓的灭不会有灭了,为什么呢?因为灭的时候就是生的时候,灭和生是一体的,灭就等于生,所以永远灭不了,永远处在生的状态,怎么可能灭呢?灭者就变成恒常了。这个第一种观察方式是把重点放在生的部分,就是灭等同于生,如果灭等同于生,那就永远不会灭,恒常安住了。如果生就是灭,它不会有生。为什么呢?因为生就是灭的缘故,生和灭是一体的,也不可能有生了,因为这一刹那当下生的时候,当下就是灭,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两种观察方式,第一种观察是把灭放在生上面,永远不会灭;第二种观察方式是把重点放在灭的上面,因为生和灭是一体的,所以既然是一体的,那么生的这一刹那就是灭的这一刹那,不可能有它存在的时候。通过以上的观察,可以成立一念心本来无生,并且不灭缘起显现,实际如水中月影一般。通过以上观察就可以成立这一念心本来是无生的。在无生空性的时候,不灭缘起显现,在名言谛当中是缘起的显现,依缘而生的心识是存在的,起作用,而且可以调伏,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的基础。但是胜义当中它是绝对、完全没有丝毫的自性。所以胜义当中是空性的,名言当中有显现,如水中月影一般,水中月影一观察就没有,不观察的时候明晃晃的显现。很多时候很多大德喜欢用水中月做比喻。因为水中月在显现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显现,但是空的时候是彻底没有自性,所以水中月可以很清楚地说明现空无二的道理。那么以上是通过运用能破抉择心性空性。下面讲第二:运用能破来抉择人无我。二、运用七相理论抉择人无我
“运用七相理论”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七相推理。以前我们讲的是五相推理,龙树菩萨的《中论》等等当中也有,很多大德解释的时候,也把它解释成比喻和意义结合起来,叫做五木车因,因为以前只是木车,现在木车也可以、铁车也可以,汽车也可以。或者七相推理叫七木车因。通过车的整体和车的分支来抉择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主要用的是五相推理,今天我们学习一下七相推理。其实七相推就是前五相的基础上再加两个,就成七相了。《入中论》云:“如车不许异支分,亦非不异非有支,不依支分非支依,非唯积聚复非形。”这里面有七相推理,车比喻成人我,它的零件、支分就是五蕴。第一相,“如车不许异支分”,不承许车和它的零件是异的。“支分”是术语,以前在《智慧品》里讲过,支分观待有支,有支和支分是一对,有支的“有”是具有的意思,具有分支的整体;支分是具有的部分。支分是部分,有支是整体。车就是有支,是整体。车和它的支分之间“不许异”,不是他体的;第二相,“亦非不异”,“不异”就是一,也不是一体的;第三相,“非有支”,这个里面“有支”不是一个词,“有”是具有的意思,“支”是分支。并不是整体的有支具有分支;第四、第五相,“不依支分非支依”。谁不依支分呢?“有支”不依支分。“支分”是所依,“有支”是能依。第四、第五是观察“能依”和“所依”的关系。“有支”不依支分是第四;“非支依”,也不是“分支”依于“有支”,不是“有支”的整体成为所依,而支分做为“能依”,这二者能依所依的关系都不存在,这是第五;第六相,“非唯积聚”,“积聚”是把所有的分支积聚起来,“非为积聚”,积聚也不是车;第七相,“复非形”,单单的形状是不是车呢?也不是车。应成车的支分之外有车,然而在车轮、引擎、钢板等的支分外,(上师已经不是解释木车了,在解释汽车,引擎、钢板这些在木车当中是没有的。)这个车和分支是不是他体?不是他体。如果车和他的分支是他体的,零件是零件,车是车,零件和车之间是他体的,那么应该是在车轮、引擎、钢板这些分支之外还找得到一辆车的存在,但是除了这些支分之外,哪还有一个他体的车呢?车是我们执著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车是存在的,是实有的。既然这辆车是实有的,那么这辆车是依靠什么有的?大家分析说,这辆车是依靠它的零件组装起来的,零件组装起来的这个东西就叫车,我们可以开,可以坐,可以买,可以卖……。那么这个车是不是实有的呢?按照月称菩萨等佛菩萨的观点,这个车是假立的,是个假象,只是一个概念而己,但是我们把这个概念执为实有了,我们认为这个车是实有的。既然认为这个车是实有的,我们就观察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实有的?所谓的车的这个概念肯定是依靠它的分支—所有的零件安立的。所以为什么要对车上的分支进行观察,因为车安立的基础就是零件,除了零件之外去哪里安立一个车?不可能把花安立成车,也不可能把这一缸水安立成车,肯定是在这个零件上面安立一辆车。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一个是我们执著车是实有的,一个车它是依靠零件而有的。我们对车和零件进行分析,如果车是实有的,那么这个车和这个零件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他体的?如果说是他体的,应该在零件之外还单独有一个车。因为是他体的,是两个不同部分,他体是什么?柱子和瓶子就是他体,张三和李四就是他体的。如果认为车和零件是他体的,应该像张三站在左边,李四站在右边,那么零件在左边,车在右边,这样是他体的,但是离开了零件哪里找车呢?离开了零件没有车。所以车和零件不是他体的。意义:蕴和我并非异体,如果是异体,应当在蕴外找到我,但找不到蕴外的我。此处的“蕴”,即五蕴,相当于车的零件;“我”就相当于这个车。我和五蕴的关系就相当于车和零件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个众生认为有我存在,我是有的。既然认为这个我是有的,那么这个我是依靠什么来安立的呢?我们说这个我是依靠我们的身心来安立的。详细分开的时候,身心就分了五蕴。身体叫做色蕴,然后心识方面有受、想、行、识四名蕴。所以所谓的我肯定是在身心、在五蕴上面安立的。五蕴就是零件,然后依靠这个零件的五蕴假立一个我的车。我们要寻找真实的我,当然要在五蕴上去寻找了。因为我就是依靠五蕴安立,所以我们要寻找我和五蕴之间,如果是实有的,应该找到一种配属的关系。我们观察到底是以什么样关系找到实有的我。如果这个我是实有的,又依靠五蕴安立,那么我们就分析,这个我和五蕴是不是他体的。如果是他体的,就像张三在左边,李四在左边,五蕴在左边,我在右边,离开了五蕴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存在,肯定是这样的,单独可以找到。但是离开了五蕴之外的我在哪里?离开了五蕴之外的我根本找不到。所以不可能是他体。我们认为,车与零件是一体的,离开了车没有零件,离开了零件没有车,它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是什么样?应成车和支分的数量相等,有多少车的支分,就有多少辆车,这和承许车是一辆相违。车是一辆,零件有很多,可能有几万个。如果是这样,零件有这么多,车只有一个,而车和它的支分又是一体的,那么有多少个零件就应该有多少辆车。因为我们有一个车的概念,有一个零件的概念,而零件和车又是一体的,所以有几万个零件,就应该有几万辆车。有多少车的分支,就应该有多少辆车,这和承许车是一辆相违。这个是我们以零件为主观察的时候,因为车和零件是一体的,所以零件有几万个,车就有几万个。那么反过来,以车为主,因为车只有一个的缘故,零件也应该只有一个零件,因为二者是一体的。所以如果是一体的,真实分析观察,肯定有很多过失。但是前面我们讲离一多因的时候,在讲一和多假立的时候,可以把很多零件组成同类,叫一辆车。这个在名言当中没有问题。也可以说这一辆车是由很多很多零件组成的,也可以说一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多组成一个一,一个一分了很多多。这是在假立当中不严格观察,世俗分析假立观察可以有,一可以很多,多也可以组成一。但是这里面是实有观察,是很严格的。如果是很严格的,必须要用最严格的程序来审查。如果车和零件是一体的,这个一是密不可分的,唯一的一,那么只有两种情况:车变成很多,或者零件变成只有一个。如果是一体,应成蕴有色、受、想、行、识五法,我也有五个;因为我是依靠五蕴而安立的,如果我和五蕴是一体的,那么粗分五蕴有五个,我就应该有五个我。如果色蕴再分下去,不止几万个。我们再比较粗大的分析的时候,我们的骨节、头发、牙齿、血液、内脏这些很多东西分出来,就几十个、上百个,然后再把它分成微尘就多的不可计数。然后感受有苦受、乐受,苦受又有无量多的苦受,被骂的苦受,骂的时候有各种各样骂你的词句而产生引发不同苦受;乐有各种各样乐的乐受,这些受非常多。因此如果是一体的,一个我应该变成无数个我了。这方面是不合理的。我们平时执著的我有这么多么?我们平时执著的我就一个,只有一个我,没有很多我。所以如果真正分析下来有很多我,那么这和我们自己的感觉、执著就完全相违了。这个是从我配属于五蕴上面去观察。反过来,从五蕴配属于我来观察,因为我只有一个,应该变成五蕴只有一个,没有五个蕴只有一个蕴了。而蕴的意思是什么?是积聚的意思,蕴就是积聚,色蕴就是很多色法的积聚;受蕴就是很多很多种受积聚。这个蕴字本身就代表多体,代表很多法的组成。所以蕴变成一个蕴,一个蕴也不符合,一个蕴都没有了,最后就不成蕴了。如果真的是独一的法,哪里是蕴呢?无分微尘不叫蕴,无分刹那也不叫蕴,它因为没有组成部分,所以不叫蕴,至少两个法以上组成的多体才能叫蕴。车是不是具有分支呢?我是不是具有五蕴呢?平时我们认为我是自主的,我具有五蕴,这是我的身体,它们是属于我的。像这样,车具有分支,车是总体,它是统摄分支法。是不是车具有分支?“具有”是指二法的相属,或者一性相属,如柱有红色;或者异性相属,如我有黄牛。所谓的“具有”是两个法之间的关系,两个法之间的相属。这个相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一性相属,如柱子具有红色,柱子和红色不是分开的,不是柱子和宝瓶的关系,而是柱子和柱子本身的颜色的关系,这个叫一性相属,或者同性相属,因明术语叫同体相属。或者是异性相属,比如我有黄牛,我和黄牛是异性,是他法。这个黄牛是我花钱买的,它是属于我的,我具有这个黄牛。像这样我有黄牛是他性的相属。相属只有这两种,没第三种。要存在这两种情况,必须有一个前提,要么是一性,要么是他性。有了一性才有同性相属,有了他性才有异性相属。因为相属就这两种,所以它的前提必须要成立一体和他体。但车和支分,既不是一体,也不是异体,故不成立车有支分。一体和他体在第一相和第二相已经观察完了,如果是一体有什么过失?而相属肯定在一体或者他体的情况下才能相属,所以既然没有一体也没有他体,那就不可能有一体相属、有他体相属。同样道理,是不是我具有五蕴呢?如果是我具有五蕴,要不然就是我和五蕴是一体的相属,要不然是我和五蕴是他体的相属,如果是一体相属,首先要成立我和五蕴是一;如果他体相属,必须要成立我和五蕴是异,但是我和五蕴一和异都没有,所以不存在这个具有的关系,我不具有五蕴。因为能依、所依都是他体的方面才能安立的。如果存在第四或者存在第五,应该变成支分和车异体。两个法成立互依,应当是异体的关系,如苹果依于瓷盘。能依和所依,所依的意思就是所依靠的处—所依靠的地方,比如房子是我们的所依,我们就是能依,我依靠房子而住;或者我坐在垫子上,这个垫子是我能坐的所依靠的地方—所依处。我是能够依靠所依的这样一种关系。或者这里面讲的苹果依于盘子,苹果放在盘子当中,盘子是所依,苹果是能依。如果要安立能依、所依,必定是他体的两个法,两个法能安立能依、所依。我依五蕴,我是能依,蕴是所依,我和蕴异体才能成立能依所依,如果我依止五蕴,如果我是能依,蕴是所依,首先要成立我和五蕴是他体的。首先成立了异体的关系,才能成立我依于五蕴,五蕴是我的所依,我是能依。因为没办法安立他体,他体的关系在第一相中就已经破完了。第一相当中就说我和五蕴不是他体的,讲得很清楚。反过来讲,蕴依于我,我成为所依,蕴成为能依,这样的关系也没有,因为这个同样要他体才能成立,只不过把顺序颠倒了一下,把我和五蕴轮流做为能依、所依来进行观察。其实不管哪个做为能依,哪个做为所依,都必须要承许他体,有了他体才有观察下一步,如果没有他体,绝不成立。所以能依、所依也不成立。以上就叫五木车因,又叫五相推求。通过五支观察,就已经完全了知这个我是假立的,我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里面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关系。其实说明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假立的,只有我是假立的情况之下,这一切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我是实有的,依靠分支找一个实有的我,怎么安立其实都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如果支分的积聚就是车,那么就成为“支分无序积聚”。把所有的零件随便堆在一起就是积聚,这个积聚是不是车呢?这个积聚也不是车。我是不是诸蕴的积聚呢?诸蕴积聚起来是不是我呢?那么如果是的话,随随便便堆积也没办法执著为我。如果支分的形状是车,在支分无序堆积时,每个支分的形状并没有改变,故应成无序堆积的支分形状也是车。比如在外面所看到的这辆车的形状,观察支分的形状是车么?还是整个形状是车?有两种观察。一个是支分堆积完之后的形状,如果支分的形状是车,那么在无序堆积的时候,每一个支分的形状并没有改变,轮子的形状没有改变,方向盘的形状没有改变,无序堆积的形状也应该变成车了,这个是肯定没办法安立的。对方说你这个是强词夺理,谁都知道无序堆积就是乱堆一起,随随便便把它乱堆到一起,就像拆解车的车间里面,所有破车的零件都拆下来堆在一起,谁会承认这是车?你这样说无序堆积是车,我们不承认。我们要说把它组装起来,轮子放到轮子的地方,方向盘应该放在它的地方,把车壳等等全部按照程序慢慢组装,通过这种一定的程序组装起来的才叫车,这种形状才叫车。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合适的。如果是支分集聚的形状,单单总的形状是车,这个也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些有序积聚的支分只是一种假立的法,依假法不会有实有的形状。因为支分堆起来的时候,形状是依靠很多分支组成起来的法,以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缘和合的法是假立的,很多分支组合起来的法也找不到实有。所以从这方面讲,依假法组装起来、和合起来的东西……他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形状可得。所谓的形状也是假立的,没有一个实有的形状。它只是个形状而己,如果形状是车,我们随便画一个形状就可以了。这个形状也是假立的,可以通过组装把它变成不同形状,形状本身只是形状而己。所以假有的形状,不可能变成一个实有的车。以上是观察七相。如果认为我是存在的,我们就通过这里面介绍的七相推理或者五相推理,反反复复地寻找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存在,如果找不到,我们只能说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我是没有的,是无我的。自续派与应成派运用五大因的差别
下面我们开始再进一步地介绍自续派与应成派运用五大因的差别。要讲中观,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自续派和应成派。在汉地,从古代到现代讲解中观并没有按照自续派和应成派的观点来区分,而是一直按照龙树菩萨的《中论》等这样解释下来,没有区分自续和应成。区分自续和应成的必要性前面我们大概提到过了,就是为了更详细地,更细致地来辨别空性。否则,我们觉得应该是空性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细微的差别,这些细微的差别如果不了解,有可能在很细微的地方,尤其在二谛方面产生一些疑惑。如果在很细微的地方产生疑惑,解决不了,我们对空性的认定还是会有很大的怀疑。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宣讲《中观》的时候,对自续派、应成派的对比非常重视。因为自续派讲解的空性,是在一般的分别念面前,认定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应成派是究竟讲空性。一个是暂时空性,一个是究竟空性;一个相似胜义,一个真实胜义。我们抉择空性是相似胜义还是真实胜义,只是破了一边还是破了四边,这个方面如果不认定,我们以为抉择空性到究竟了,其实根本没有。如果我们不学习自续派、应成派的差别,如果我们只是有一个相似胜义,我们以为这个相似胜义就是真实胜义,那么对我们抉择大空性,尤其是最后要趋入密宗的修法4,会耽误我们的时间。最了义的法再配以最利的根基,成就的速度就很快;如果最好最究竟的法配一个最钝的根基,不起作用;一个很利的根基配一个一般的法,对他的根性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什么是了义的,什么是不了义的,然后我们的根基如果够利,就应该接受最了义、最究竟的法,因为我们可以接受、可以修行,可以抉择。在这样基础上,我们认定烦恼的时候,认定这个空性越究竟,越会认定烦恼是无自性的,是虚假的。就像慈诚罗珠堪布讲的,痛苦、烦恼是纸老虎,怎么去认定它是纸老虎?因为它就是假立的,本来就是无自性的。在大空性的基础上再来看这些东西,的的确确没有丝毫的自性,没有丝毫的本体。而且如果我们给别人介绍的时候,把相似的胜义介绍成真实的胜义,本来是相似的胜义,我们说这个是真实胜义,那也有可能误导别人的,因为他的根基有可能能够接受最了义的观点,但是只是把相似的东西给他介绍成了义,这个也不合适。所以从自利和他利的角度来讲,分析清楚自续、应成这些空性方面的微细差别其实很重要。一、略说应成理论和自续理论的差别
五大因是自续派和应成派共同运用的理论,但二者运用五大因进行抉择的方式,却有本质性的差别。前面我们说共同理论,自续派和应成派共同使用这个五大因,虽然是共同的,但是里面也有不共的,所以二者之间有差别。虽然说共同,都在应用,但是使用的方式、方法上面不一样。我们说这个武器是共同的,但是怎么去使用它?力量大、技术好的人使用这个武器就不一样,能够把这个武器发挥得淋漓尽致,发挥到最大作用,而其他人使用的时候可能笨拙一点。所以都在用这个共同理论,但是使用的方法上面、抉择的方式上面的确不一样,有本质性的差别。自续理论是眼等有法在自他前共同成立的前提下,承许所立,如胜义中无生;下面提到一个三相理论。三相理论当中第一相是有法5。比如眼等无自性,因为是离一多故。眼耳等这些显现法是有法。它是要观察的基,要观察的地方,所以称为有法。这个是自他前共同成立的。比如如果我们要辩论有法—花是实有的还是无实有的,首先我面前的花和你面前的花要达成共识,这个有法—花在你我面前都共同承认。“承许所立”的所立是什么?花是无自性的,或者这个花在胜义当中是无生的。“胜义中无生”就是所立—所成立、所安立的宗。花是有法,胜义中无自性是它的所立。“承许所立”,所立也承认,“如胜义中无生”。能够成立这个花无自性的根据,叫能立的因。能成立它无自性的这个理由、根据,也是自他共许的。比如离一多故,离开一,离开多,我也承认,你也承认。大家共同承认的时候,这个能立就成立了。比喻也是自他共许的。比如宝瓶、彩虹、其他的法,这些比喻也是自他共许的。“因和所立一者有则另一者有、一者无则另一者无的关系”“因和所立一者有则另一者有”在因明三相当中叫做同品周遍。“一者无则另一者也无”叫做异品周遍。三相观察是因明中经常使用的观察方式。
也在二者前共同成立6。总之,承许三相和比喻在自他前共同成立的理论,是自续理论。三相推理首先要成立宗法,然后成立同品周遍,再成立异品周遍。简单介绍一下三相推理。比如惯用的比喻:柱子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个就是一个三相推理。柱子是有法,又叫所诤事。这个柱子是大家都看到的,但是对于它的所立—柱子是无常还是常有的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要辩论。自宗的所立是柱子是无常,但是这只是一个立宗,这是我们自己的观点,用什么来证成这个观点呢?使用能立的因—所作性故。所作性就是它是因缘造作的,柱子是一棵树,树需要种子、养分、时间成长成树,然后伐木工人把树砍下来,木匠要加工,把树皮去掉,刨圆,晒干,然后做成柱子的形状,所以这个柱子是所作性。是所作性的缘故,它肯定是无常的。这个叫做一种推理。我们要推理柱子是无常的,用所作性故来推理。这个里面有三相推理,首先第一相是宗法推理,观察方式是把能立的因—所作性,和有法—柱子放在一起观察成不成立。柱子是不是所作的,对方说柱子是所作的,这就成立了。第一支必须要这样成立。这个叫宗法。三相当中第一相宗法成立了。也就是我也承许柱子就是木匠所作的,因缘所造的,他一观察,柱子的确是所造,这个就是第一支,必须要成立的。如果这一支不成立,下面不用观察了。首先要花时间把第一支共同承许了。第二支讲同品周遍。同品周遍就是观察因和所立之间的关系。所立是什么呢?所立就是无常。柱子是无常,这个无常就是我们的所立,我们要安立这个宗。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能立根据,即所作性故。因和所立一者有,另一者也有,这个叫同品。这个因如果是所作性的,周遍是无常的,决定是无常的。这个时候因—所作如果是存在的,另一者它的所立—无常一定成立。所作性和无常二者之间是同品周遍的。这个就是第二相,因和所立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能立的因成立,所立就成立。所作性的法周遍都是无常的,这个就是因和所立一者有另外一者有。第三相是一者无另一者也无。这个也是因和所立的关系,但是反过来讲,所立的法一退失,能立的因肯定也跟着就退失了。这是异品周遍,异品就是它相反的方向。无常相反的方向是什么?是常有,无常一退失,就变成常有。所有的非无常法周遍是非所作性的,这个成不成立?虚空、石女儿是不是非所作,是不是非因缘所造的?这个一成立,三相就成立了。这个因就是正确的因。第一个因在有法上安没安立;第二相因和所立之间有没有同品周遍;第三相,所立退失,变成反方面,无常变成常有了,它的能立跟不跟着变成反方向,如果所立无常变成了常有,变成了异品,那么它的所作性也跟着变,也变成了异品,它的异品是什么?所作性的异品就是非所作。所以如果是常有的法,周遍是非所作性的。这样一观察,因就是正确的了。所以要安立一个事情必须要通过这三支来观察,如果全部都成立了,这个就是正确的,如果其中哪个地方有毛病,这个逻辑就是有漏洞的。以上再加一个比喻,如宝瓶,叫做三相推理。下面还要讲很多三相,到底什么是三相。有些地方讲因三相,因三相第一相就是有法;第二相就是所立;第三相就是能立。这个叫因三相,就是因的三个相。三相推理就是前面讲的一样,首先是宗法,能立在有法上面安立,然后是同品周遍,能立和所立之间是不是同品的。然后异品周遍,如果所立一退失,能立会不会跟着退失,异品是不是同样周遍的。如果没有,那么就是不成、不定,或者相违,就出现这些问题了。像这样有法自他承许,同品周遍自他承许,异品周遍自他承许,比喻也自他承许,这些就叫自续理论。自他都承许的推理的过程,和推理安立的法,叫自续理论。应成理论是在自己没有任何承许的前提下,仅仅运用他方前成立的三相和比喻,对敌宗发出自许相违等太过的理论。应成派也使用这三相理论,但是应成派使用三相理论的时候不是说自他共许的。前面的自续派是自他共许,我和对方都要承认,我让对方知道这个法是空性的,我承认这个,他也要承认。应成派是怎么样的?应成派根本没有任何承认,安住在大空性当中。所以有法也是对方承认的有法,然后能立、所立都是对方面前成立的因。所以他只是使用对方成立的三相来推翻对方的观点,这个方面就叫做应成理论。他自己没有任何承许,没有立宗,只是借用了对方成立的三相。对方对他的三相是承认的,应成派和对方辩论的时候,虽然也使用,但是使用的时候,所使用的有法,比如花,其实在应成派抉择空性之前,他没有预期这个花是存在的,在他的境界当中,所有的花都不存在,但是对方面前有花,所以借用对方面前花这个有法,来说“花是空性的,无四边生故”,或者说“花是空性的,离一多故”。花也好,空性也好都是对方的承认,他自己其实没有一个对空性的承许,然后离一多故也是对方的承认,所以这个叫做他称三相理论,而不是自许的。“仅仅运用他方前成立的三相和比喻,对敌宗发出自许相违等太过的理论”,是应成派四大不共因当中最后要讲的第四个因—他称三相理论,也就是在他人面前才能成立的三相理论。下面还要详细地介绍。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2无实有的意思是以如梦如幻的方式起作用。
3二者:心识和不相应行。
4密宗的修法是在大空性的基础上安立的。
5有法:又叫宗法。
6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也在二者前共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