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贤劫第四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然要了解本师的大愿大行,以及福慧资粮圆满后在此界示现成佛的传记,这个道理是十分显然而重要的。只有释迦佛发五百大愿来摄受苦难深重的娑婆世间人寿百年、五浊炽盛时期的我们,这个世界如此浊恶不可救药,以至诸佛都没有发心摄取此界有情,释迦如来却以极重的悲心要救度这些善根烧灭的有情,经过旷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波罗蜜多的修道,终于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成为整个教法期圆满的导师。可以说,此世间一切三宝的事业都是释迦如来悲愿的呈现,因此我们能在三宝光明的照耀下入于光明的佛道,下至听闻一句光明法句,得到解脱与菩提的因缘,完全是释迦如来的大恩,因此我们不能不了解本师佛的三种经典:
宣说本师佛为救度我们旷劫前发白莲花大愿摄受此界众生而示现成佛的大经——《悲华经》
宣说本师在无量劫中修行六波罗蜜多菩萨行海的大经——《六度集经》等
在因缘成熟之际,佛亲自现身此界八相成道的行传——《过去现在因果经》等
首先应当常随本师释迦佛学,由于有最切近的摄受的因缘、恩德的因缘,应当首先敬礼释迦如来。本师在无量劫来示现如何发心、如何行道,总的是我们菩提道的最佳典范,如果仅是一些粗浅的理论“我如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或者“以入大地菩萨的大行作为所愿境”,心中没有一个鲜活的、传神的本师佛的佛心佛行的描写,那我们就容易落于干枯,而所谓的怎样将生命灌注于菩萨的大心大行等,也很难有切实的随学之处,因此需要以学习佛的《六度集经》来引领我们进入到真正的菩萨大行中。
修习常随佛学的发愿,典型的轨道就是佛怎么发愿、怎么修行、怎么成道,乃至佛的名号、寿量、刹土、事业,我都发心达到同样的境界。为了使这样的发愿不落于口头,不得不去了解佛到底是怎么发心、怎么行道的。扪心自问,我们对佛的印象、对佛的感情、对佛的随学,是不是远远不如对世间名人的印象、对他的感情、对他的随学?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认识,缺乏真正佛心佛行的境界融入我们的心灵,这样就距离相当遥远。单是口头念那些句子,发不出相应的心,也仍然差距很大。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为了真正生起对佛的信心,从而有真正的皈依佛的心,乃至皈依三宝的情操,再往上如何出离、如何为菩提而发心行道,一切都要以佛为楷模,这一切该如何走,首先应当从相关的三部经典入手。
这是距今一千八百年左右的极早时期的翻译,译师是三国年间的康僧会,他在佛教史上有崇高的地位,由于他的努力,在三国的东吴出现了沙门和佛教寺院,他的精诚竟然感得佛舍利降临,这让吴国国主孙权生起了信心,此舍利冲下时能冲破铜盘,即使力士用力砸,也丝毫无损。他建立了沙门的道行和形象,促使孙权建造了佛教的第一座寺院,称为建初寺,后来他又感化了第二代国主孙皓,可以说东吴一带佛法的兴起,康僧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再者,他的翻译几乎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旷古以来释迦如来行道的事迹,以此种翻译文字竟然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移到我们的心前,当我们安下心来静心一读,这一个个的公案就会领着我们走入佛的大心大行的境界,是如此地寂静、如此地深远,没有距离。释迦如来如何行六波罗蜜多的道行风貌,恍然现在心目之间,就像自己与公案中的菩萨在同行六度那样,身临其境,这是由于翻译的意境极高,有传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只要置身于本经典中,就能亲切体会到释迦如来的佛心佛行,效果当然是非常好的。比如,当心至诚的时候,常常会为佛的可歌可泣的菩萨行感动得落泪,会彻底被佛的善心所感化,由此对佛的信心、对佛的皈依心、对佛的随学心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意境加持下来,自然就很深信佛历劫的大悲愿行,以这个心灵的触动使得我们发生善根,就会发愿来随学释迦如来:自己也要这样来发起悲心,这样来行持菩萨道,并且尽未来劫圆满菩萨的愿行。而且由于对佛心佛行有亲切的认识和体会,就会对于佛的大愿生起决定的信心,会认为佛就是这样发愿这样行的,决定就是最圆满的导师,有了这样的信心,那当然就入了皈依、入了随学,这样所有公案的呈现就不只是学学故事,而全数成了要跟着走的路。
我们的心总是会处在偏见的状态,这个心不能轻信,常常认为好的不一定好,认为坏的不一定坏,一个初次的感觉不能代表最终的结论,一个方面的认识不能代表整体的情况。对于《六度集经》,一般看起来会以为这个怎么这么古奥、生疏,不想看,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首先,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要从整体上看、从内涵上看、从真正的对于心的饶益程度、深远的结局上看,先排除一些小的分别,要理解这是快接近两千年前的翻译,那时处在最早期,各种词汇还没有定,诸如泰山地狱、三尊、众祐等的词汇属于早期翻译,还有一些是结合本土的翻译,沿用本土的常用名词,词语生疏的障碍实际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对这些词语基本作了解释,习惯的问题快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过去,我们不能因为这几小时适应的问题就认为有非常大的障碍、非常多的难懂点,这种看法属于分别心不公正的偏见。所谓对古经的看法,不一定是古的就不好,新的就好,也不是新的就不好,古的就好,而是要看它实际的价值。不管怎样,我们需要去尝试,表面的看法往往是在欺骗自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无价之宝的古玩,浅薄者会认为这还不如一个儿童玩具新鲜好玩,而实际上它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霜,是一个古旧的相,但内涵却很深,具有比儿童玩具大一亿倍的价值。为何选择这部古典的佛经来学习,并且也劝导大家克服几小时的难关,来达到一个深远的效果?佛陀传记的翻译可以说极难,也可以说极易,难与易的判断需要从标准来看。假使只是停留在简单叙述,那好像谁都能够讲讲佛的传记、各种六度的故事,下至乡村老妇也都讲得来很多,这叫极易。极难,是指意境,要想传神非常难,原因要这样认识:这里要能传出佛心佛行的境界,传出释迦佛旷劫行菩萨道的境界,请问译者没有自身高度的素养和修行,可能达到吗?比如说,假使作者、译者或影视演员自身体会不到善人的境界,那么能很好地诠释出一个善人的形象来吗?善人尚且如此,再提升到菩萨道的心胸、愿力、行六度的那种伟大的心行,假如译者没有相当的量,心尚且不知,怎么能用另一国的语言表现出来呢?因此要广大地弘扬释迦佛的菩萨行传,就需要有一个高标准的选择。这个道理也很明白,假使在这个文字本身上面就没有菩萨大心大行的境界,那么在这些文字的缘起上面再怎么读也不可能有,就算学无数遍,也不可能出现,好比无数沙子里面没有油,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挤出油来。这样去衡量的时候就知道,从古至今有非常多的释迦佛本生传的翻译和写作,与《六度集经》的意境相比,有些相差非常远,有些也达不到,这样就知道康僧会大师了不起的修证和译经的境界。这部经流传了将近两千年,它是千年瑰宝,经过了历史的验证。之所以选择这部佛经,是由于它有传神的境界,好比我们几十年学佛都没有接触到这样的经,由于没有相应的助缘,也难以知道佛心与佛行的境界,这就像喝一亿次的自来水,也没有得到甘露的品味,既未得到这种品味,也就不会发生滋润身心的妙用,相反,只要有一次领受到了甘露,那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作用。从这样的比喻就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够深入进去,那我们有可能在这一次当中,就在心里深深地印下佛的心行,心中有了这个根本的种子,那就会对释迦佛产生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感动,从这里就会出现真正的皈依佛的心,愿意永远跟着佛走,并且真正生起献身佛教的心,这个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根本性的塑造,要知道真正生起一刹那的信心,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原因就是很多次没生过,生了以后再来随念佛,以及做各种各样的法行,礼拜也好,赞颂也好,念名号也好,念心咒也好,住持佛法也好,有这种根本的信心,任何一个都是不可思议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应当克服暂时几个小时的困难,主动地投入。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个经本里面具有加持,能传出佛心佛行,只要好好地读,好好地学,由于有,就一定会得到,而且一次一次都会得到,这样一次一次地积累,就会在心里种下很好的善根,出很好的道心、与佛相应的心,而且不必有什么顾虑,也无须太多的怀疑,只要我们坚持去走,就可以用事实来证明。附带讲一句,《悲华经》也同样地好,文字的微妙的确能传出佛的悲愿,再学习《悲华经》,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真正地认识释迦如来,心里会有真正的感动,我们作为佛弟子都需要走这样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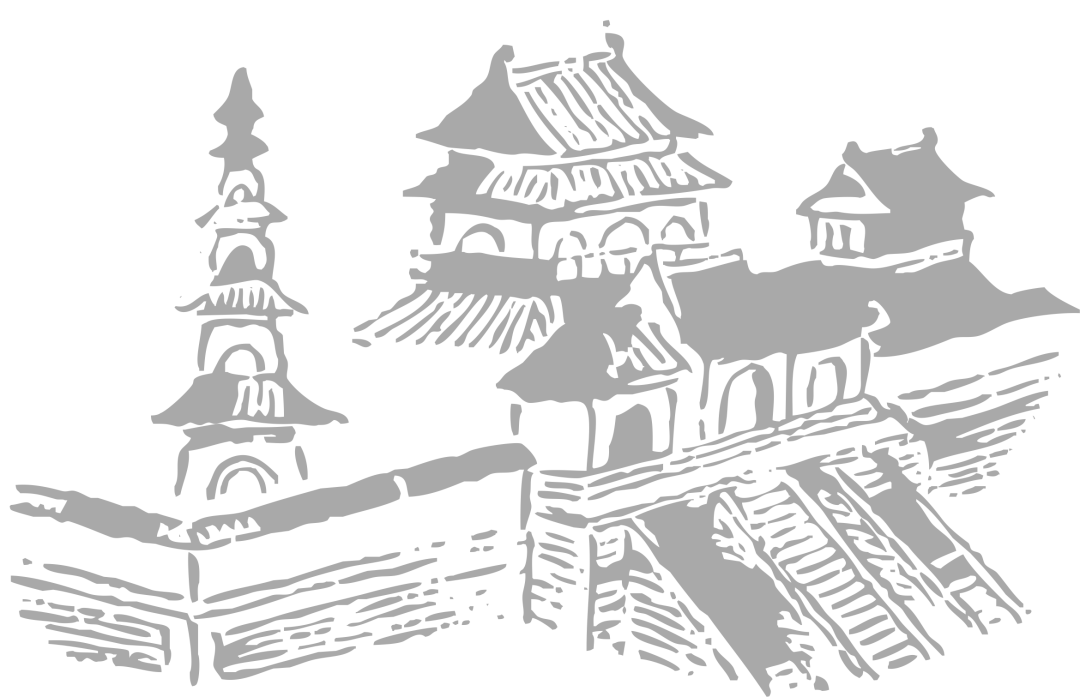
译师康僧会,祖先是康居人,世代居于印度,父亲因为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在僧会十一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服孝完毕后,他就出家了,修行策励精进,要求自己很严格,为人心量宽广,有很深的见识,勤奋好学,通达三藏,而且他的涉猎很广,博览儒家六经,天文地理很多都有涉及,能辨别玄奥,颇有文采。
当时三国年间,孙权已治理江东,佛教还没流行。先有月支国的支谦居士来游历汉土,他依支亮学法,博览群经,无不精深研究,他多方面学习世间技艺,精通六国语言,由于避乱而来到了吴国。孙权听闻他的聪明才慧,就召见了他,拜他为博士。支谦以大教虽然行于吴地,但是经书多是梵文,翻译得很不够,而自己已经善巧了此地方言,于是就收集了很多经书译为汉文,数年间,翻译了《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瑞应本地经》等共四十九种,他还制定梵呗,注解《了本生死经》等,都流行于世。当时东吴之地虽然初步接触了佛法,但教化尚未普及,僧会想使佛教振兴于江东,关键之处首先要建立佛寺,于是他游行东国,在吴朝赤乌十年抵达建业(今天的南京),建立茅蓬,设立佛像修行。那时的吴国人因为第一次见到沙门的形象,不知道他是什么道行,怀疑他标奇立异,结果就上奏说:“外国人进入境内,自称为沙门,但看他的容貌、服饰都不正常,应当严格检查。”那时的皇帝是孙权,他说:“从前汉明帝做梦,见到名称为佛的神,这个沙门的行事是不是佛遗留下来的风规呢?”就召来僧会查问:“你有什么灵验?”僧会说:“如来涅槃转眼已经一千年了,遗留下来的佛骨舍利应着众生的机缘而示现教化的神迹,往昔阿育王启建八万四千舍利塔,由兴起塔寺可以表明是佛遗留的化迹。”意思是由佛遗留舍利,可以证明如来的出世。孙权认为此种神化太过于虚夸、怪诞,就对僧会说:“假使你真的能让我得到舍利,我一定建塔供养,如果是虚妄,那我国也有常规的刑罚。”意思是,假使属无稽之谈,将以刑罚处置。僧会请求给与七天的期限后,就对眷属们说:“佛法的兴废在此一举,如果现在不至诚,后面将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与眷属共同斋戒清洁,处在净室中,将一铜瓶放在供桌上,烧香礼拜,请佛感应。七天期满,没有任何动静,又求延期为两个七,仍然如此。孙权说:“确实是欺诳。”就要加之于罪。僧会又请延期至三个七,孙权特别开许。僧会又对眷属说:“孔子有言,文王已去世了,文明礼乐不是还在我这里吗?法灵本来应当降下灵应,若我们不能感通,何必假借王法呢?我们应当以誓死为期。”意思是若不能感应,宁可自己死掉。到了第三个七夜幕降临之时,还是没有动静,大家无不恐惧震惊,直到入了五更天,忽然听到瓶中“呛”的一声,僧会亲自去看,果然得获舍利。第二天早晨僧会以舍利呈视孙权,整个朝廷都集合来观看,当时炽然的五色光明照耀在瓶子上,孙权自己以手执瓶,瓶口向下,将舍利泻于铜盘上,只见舍利冲下来连铜盘都破碎了,孙权肃然起敬,惊叹而说:“真是稀有的祥瑞!”僧会又说:“舍利威神岂止是光明之相?劫烧之火不能烧,金刚之杵不能碎。”意思是舍利为佛的愿力所在,它的威神哪里只是显现五彩的光相呢?劫灭之火能烧须弥也烧不了舍利,金刚杵能碎巨山也不能碎舍利。孙权就命令再作试验,当时僧会起愿说:“佛法才被于此方,众生正仰赖佛的恩泽,愿佛再垂下神迹,充分地显示佛法的威灵。”说后僧会将舍利放置在铁砧磓上,让大力士猛力击打,当时铁制的砧磓都打得凹陷下去,舍利却毫发无损。孙权大大叹服,当即就下令为舍利建塔。这是东吴之地最初建有佛寺,因此取名为建初寺,此地则称为佛陀里,从此江东之地大法兴起。到了孙皓即位持政时,法令暴虐苛刻,废弃天下的祭祀,连带佛寺都想一并摧毁。孙皓说:“这个是由什么原因而兴起的?如果这个教是真的,与儒家圣典相应的话,应当准许存在,信奉其道,如果纯属虚妄不实,那就全数焚毁。”大臣们都说:“佛的威力不同于其他神灵,由僧会感得瑞应,先皇创立寺院,现在如果轻毁,将来恐怕要后悔的。”于是孙皓就派遣具辩才的张昱去寺院向僧会问难,张昱从各方面质问,僧会都一一应机回辩,有锐利文理的锋芒,就这样从早至晚一整天,张昱终究无法胜伏。辩论完毕后,张昱要回去,僧会就送他到门口,当时见到寺院旁边有做祭祀的人,张昱就说:“佛的教化既然很信实,为什么近旁的此辈却不能革除?”僧会说:“雷霆虽然能震破群山,但耳聋者丝毫不闻,这并不是雷霆的音声小。假使理上相通,纵然相隔万里,也能即时相应,而如果心地阻塞,哪怕像肝与胆一样邻近,也如同楚国与越国一般格格不入。”张昱回来后,感叹地说:“僧会的智慧不是我所能揣测的,愿皇帝明察。”于是孙皓就大集朝中贤士,隆重地以马车迎请僧会。僧会入座后,孙皓就问道:“佛教所说的善恶报应阐述的是什么道理?”僧会对答说:“世间的明主以孝慈训导世间,天空中就会出现赤乌飞翔,见到老人星(即南极星),以仁德辅育万物,则出现涌出甘泉、生长嘉苗的瑞应,既然善会有这些祥瑞的感应,那么恶当然也跟它一样,因此,隐处作恶,会被鬼神伏获而诛罚,显处造恶为人所见,则作刑法的诛罚。易经说到‘积善余庆’,诗咏有言‘求福不回’,此虽是儒家经典的格言,实际也是佛陀教法的明训。”孙皓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周公、孔子的教化就已经阐明了,哪里还用得着西域佛的教法?”僧会说:“周公、孔子的法言只是简略地显示了近前因果律的迹相,至于释迦如来的圣教,则极为完备地揭示了人所不见的深远之事,因此说到造恶出现地狱的长苦,修善获得天宫的永乐,这样显示因果律的事实来教化人心,断恶修善,难道不是更为广大的善法吗?”当时孙皓无以反驳。孙皓虽然听闻了正法,但却难以改变他昏昧暴虐的个性。后来,他让宿卫兵进入后宫整理园地,结果得到了一尊高数尺的金像,就呈给孙皓,孙皓让人把这个金像放在有粪便的地方,用污水淋灌,然后跟群臣们一起笑乐。忽然之间,他的全身浮肿,阴处尤其痛,哀嚎声响彻虚空。婇女当中有信奉佛法的,以此而来探问说:“陛下在佛寺中求福了吗?”皓抬头问道:“佛的神异大吗?”婇女说:“佛是大神。”孙皓当时就醒悟此话有意,因此婇女就迎来金像安置于殿上,以香汤数十遍地洗过,烧香忏悔。孙皓则叩头于枕,陈述自己的罪状。过了一会儿,疼痛就有了间隙,他就派使者到寺院问讯道人,请僧会来说法,会当即就随着进入宫庭。孙皓具体请问罪福的原由,僧会为他作开演分析,言语精要。由于他先前就有些理解,如今再听心里非常欢喜,就求看沙门戒,僧会说:“戒文要保密,不能轻宣。”就取本业一百三十五愿,分成二百五十种事,行住坐卧都愿众生,也就是像《净行品》那样,无论行住坐卧都发利益众生的愿。孙皓见到佛门慈悲愿力广大,更加增上他的善意,当即就从僧会受五戒。过了十天,病就痊愈了。孙皓就对僧会的住处加以装潢修饰,宣布皇家的宗室都要供奉僧会。僧会便在吴国朝廷宣讲正法,但由于孙皓性情粗犷凶暴,他的心还不能接受妙义,因此只能讲述近前的因果报应之事,开导其心。僧会在建初寺译出各种佛经,如《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等,又译出《小品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翻译都达到了微妙,契合经义。又传泥洹的梵呗之声,清靡哀亮,成为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三经,而且制定经序。他的著作都语言文雅、明显、涵义微妙,这些都流行于世。到了吴国末年天纪四年四月,孙皓向晋朝投降,九月,僧会得了一场病,然后圆寂。到晋成咸和年间,苏峻作乱,焚毁了僧会所建的佛塔,司空何充再作修造。当时有一位平西将军赵诱,向来不信佛法,傲慢三宝,他进入这个寺院,对道人们说:“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这是虚诞不经的说法,谁能信呢?如果能让我亲眼见到,那我当然没话说。”说完当即佛塔就放出五色光明,照耀整个殿堂寺庙,赵诱肃然起敬,汗毛都竖立起来,由此就信敬三宝,并且在寺院的东边又建了一座小塔。这远是由如来神力所感,近也是由康僧会大德的道力,因此就画了他的像,流传至今。